第一节 可视错觉与新的心理学
1910年仲夏,在一列从德国中部飞驰而过的火车上,一位名叫麦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的年轻心理学家远眺窗外的风景。尽管电线杆、房舍和山顶是静止不动的,可看起来却似在与火车一起飞奔。
这是为什么呢?
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错觉,也都视其为想当然,但韦特海默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这件事必须有个解释。这个疑团使他联想到另外一种错觉运动——频闪观测仪。它的基本原理与电影差不多,作为一种玩具在当时非常流行。不管是电影还是万花筒,都是一系列以几分之一秒的时差所留存下来的照片或展示其最细微变化的画面快速地在眼前通过,给人留下连续运动的印记。
几十年来,这种现象广为大家所知,却从未有人给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就是在这辆火车上,刚刚在魏茨堡获得博士学位的韦特海默突然直觉上意识到答案所在。他突然意识到,运动错觉的成因可能并不发生在许多心理学家所认为的视网膜上,而是发生在意识深处,极有可能是某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在连续的图片之间提供出转接,从而对运动产生了感知。
当时,韦特海默正在维也纳大学就阅读恐惧症进行研究,此番正要赶往莱因兰度假。这一想法使他激动异常,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在法兰克福跳下列车,前去拜谒弗里德里奇·舒曼(Friedrich Schumann)教授。他是感知方面的专家,在去魏茨堡之前,韦特海默曾与其一道求学于柏林大学。
进城后,韦特海默去玩具店买了一只频闪观测仪(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是一种流行玩具,可以产生连续活动的印象)。这只频闪观测仪中有马和小孩的图片,如果控制好速度,就可看见马在行走,还可看见小孩子在走路。韦特海默用纸片代替那些画面,并在纸片的两个位置上画一些彼此平行的线条。他发现,用一种速度转时,他先看到一根线条,然后才在另外的地方看到另一些线条;用另一种速度转时,两根线条则平行在一起;再换一种速度转,有一根线条从一个位置移动至另一个位置。就这样,他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验,一种全新的心理学理论即将产生。
第二天,韦特海默打电话给法兰克福大学的舒曼,告诉他自己的猜想,征询他的看法。舒曼解释不出所以然来,但同意让韦特海默使用他的实验室和设备,包括他亲自设计的新型速读训练器。速读训练器可精确地控制频闪观测仪只能粗浅演示的实验。
韦特海默需要一些志愿者充当实验的受试者,舒曼便找来自己的助手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ohler),苛勒又介绍来另一位助手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他们两个比韦特海默年纪要轻(他30岁,苛勒28岁,考夫卡24岁),但三人都对神经心理学中的新心理学派和冯特的门徒们所忽视的高级精神现象极有兴趣。他们立即着手工作,此后成为终生的朋友和同事。
韦特海默没成婚,还有一份额外收入——父亲为布拉格一所商业学校的校长——因而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度假计划,在法兰克福一待就是半年。他让苛勒、考夫卡和考夫卡妻子充当受试人,进行一系列实验。
按照在旅馆里所做的初期实验模式,韦特海默的基本实验是轮流投影一条3厘米长的水平线条和另一根在它下面的约2厘米长的线条。在投影速率较低时,他的受试者先看到一条线,然后是另一条线;速率较高时,两条线可同时看到;速率中等时,一条线平滑地向下面的线条移动,然后又返回。
为变些花样,韦特海默使用一根竖直的线条和一根水平的线条。速度刚好时,他的受试者可看到一条线以90度的角度来回运动。在另一个变换中,他使用了许多灯。如果速度恰好达到临界点,那么,看起来就像是只有一盏灯在移动一样。他还使用了多根线条,并将之涂成不同的颜色,设计成不同的形状。在每种情况下,它们都能制造出运动的错觉。即使他将正在进行的事情告诉3位受试人,他们也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在其他许多种变换中,韦特海默都力图排除此类现象是由眼睛运动或视网膜残留而引起的可能。
他得出的结论是:运动错觉的发生不是在感觉的水平上,不是在视网膜区,而是在感知中,在意识中。在这里,由外面进入的、互不关联的感觉被视作一种组织起来、具有自身意义的整体。韦特海默将这种总体感觉叫作格式塔,一个德语词汇,原意为外形、形状或配置,他在这里用以表示被作为有意义的整体而感知到的一组感觉。
这样看来,他花费数月所进行的工作似乎只是解释了一个小小的错觉。但在实际上,他和同事已埋下了心理学中格式塔学派的种子,它将形成一个运动,该运动将极大地丰富和扩大德国和美国的心理学内容。
第二节 思维的再发现
韦特海默的理论是,思维让进入大脑的感觉有了结构和意义。这一认识显然走出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往往与格式塔疗法相混淆,前者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后者是心理疗法的技巧。
当时,自然科技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电灯正在快速地改变城市甚或遥远乡镇的夜生活,汽车也正在改变各个国家的习惯,飞机已可以进行长距离飞行,玛丽·居里刚刚分离出镭和钋,卢瑟福(Rutherford)正在编制原子结构理论,齐柏林(Zeppelin)客运服务开始起步,黎·德·福里斯特(Lee De Forest)的晶体管也刚刚申请到专利。新的心理学与这些发展相辅相成,心灵主义心理学则比以前更为形而上,更不科学,因而更像明日黄花。
心理学领域,其他研究者也不断地提出证据,证明感知与视网膜或其他感官接受到的感觉并不一致,认为感知是思维对这些感觉中数据的解释。
远在1890年,奥地利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埃伦费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就已指出,当乐曲变调时,所有的音符都已改变,可我们听到的却是同一个旋律。因为我们辨识音乐是由思维而不是耳朵。
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医生厄恩斯特·马赫(Ernst March)于1897年说道:当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一个圆圈时,它总是圆的,但在镜头上观察时,它却是椭圆的;当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一张桌子时,视网膜上的图像改变了,可我们在内心里体会到的、看见过的桌子的经验并没有改变。思维在解释感觉时将按自己所知道的目标形状进行描述。
1906年,维托里欧·本鲁西(Vittorio Benussi)进行了著名的穆勒-里尔错觉实验。实验中,两条线(如下图所示的平行线条)在长度上看起来有所不同,而实际上它们是等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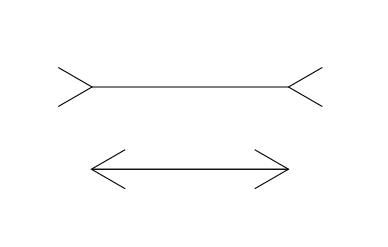
图 1 穆勒 - 里尔错觉
他发现,即使他告诉受试者集中精力于平行的线条,他们还是无法使自己忽视整个图形。他们可以减少错觉,但不能消除错觉。
韦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在接受培训时早已熟知了这些发现与概念。此后,三人都进行过包括较高级精神功能的研究:韦特海默研究过有阅读障碍、思维迟钝的孩子和病人的思维能力,考夫卡的博士论文是格式塔式节奏形态,苛勒研究的则是声响心理学。
然而,这样一个志趣截然不同的三人小组,乍看起来,还达不到彻底击败冯特心理学的智力水平。
在布拉格长大的韦特海默是个犹太人,长相颇具孩子气,头顶略秃,蓄一脸毛乎乎的、元帅般的大胡子,但骨子里有股诗人气质,有音乐天赋,热情,幽默,个性乐观。他富有煽动力,当然也有口才,脑子里总是闪现出新的念头。然而,他非常不擅于写作。
柏林人考夫卡只能称得上半个犹太人。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瘦长的脸上写满严肃,性格内向而敏感,且极易动摇。但使人无法解释的是,这些特点尽管使其上课干巴得味同嚼蜡,却对女学生极具吸引力。尽管他在讲台上浑身都不自在,但在写字台上却是游刃有余,不断地炮制出一系列格式塔心理学的学术报告。
苛勒则出生于爱沙尼亚,不是犹太人。他在德国的沃尔芬布特尔长大成人,脸上呈现出好斗的表情,硬邦邦的短发在中间分开。他是三人组中最刻苦的实验者,后来到一所研究院工作,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他高傲、古板,为人正派——对于结交10年的朋友,他才肯使用“你”来替代“您”——但在写作中,他的文笔总是令人意外,感到既放松又使人着迷。
然而,三人性格及爱好的不同却能使其各司其职,取长补短,从而结出难以意料的硕果。格式塔心理学史的一位研究者认为,韦特海默是“智慧之父、思想家和革新者”,考夫卡是“该组的销售者”,而苛勒则是“内勤人员,干实事者”。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格式塔心理学成为德国心理学的主要力量,也成为其他国家不断成长中的心理学流派。但它对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且大多发生在1927年至1935年间,也即三人全部来到美国之后。尽管三人均没有在美国心理学的机构中担任要职,但他们的思想已渐渐地充斥于心理学之中,并发展壮大,直逼行为主义的营垒。
第三节 格式塔定律
从一开始起,韦特海默就认定格式塔理论并不仅限于对感知的解释。他相信,它将能证明自己是学习、动机和思维的关键。
他的这些认识建立在自己的一些早期研究之上。他在法兰克福就运动错觉进行研究之后不久,受到维也纳精神研究院儿童诊所主任医师的邀请,到那里寻找对聋哑儿童的教育方法。他的实验方法之一是,由自己搭建一座简单的桥,桥上有3块木板,建桥时,一位聋哑儿童看着,然后由他拆下来,再让他试着搭建。通常情况下,犯过一至两次小错之后,他将学会并成功地搭建几座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桥来。在韦特海默看来,孩子的思维并没有建立在对演示中所使用的物品的数目和大小的感知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某个稳定的配置的感知之上,该配置即是格式塔。搭桥即是这种模式,两个同样长短的长条物水平定位在两个终端。
韦特海默还阅读人类学就原始部族的数字思维所做出的报告,并收集到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外加他在法兰克福所做的实验,使他于1913年在一系列讲座中勾画出一种全新的心理学轮廓。他认为,格式塔并不是相关联想物的累积,而是某种整体架构,因而要将事物看作一个有序的整体。
尽管韦特海默认为格式塔理论是整个心理学的基础,但他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应付感知问题。在十几年的时间里,3位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发现了一系列的感知原理,或被称作“格式塔定律”。韦特海默总结了自己和他人的一些观点,在1923年所发表的为数有限的几篇论文中对若干主要定律一一命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下列几条。
就近律:在观察一系列类似物体时,我们倾向于以彼此距离较近的组或集对它们进行感知。韦特海默的简单演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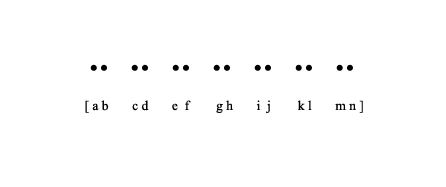
图 2 就近律:简单例子
他发现,给人们看一排黑点时,他们会自发地以彼此距离最近的黑点结对来看(ab/cd/……),但实际上,完全也可看作一对分隔较远的黑点和分隔较近的黑点(a/bc/de/……)。然而,没有人以这种方式去看,且大多数人无法使自己这样来看。还有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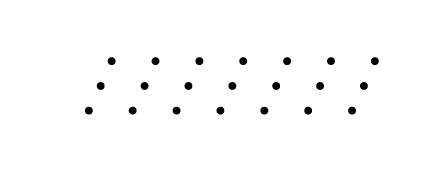
图 3 就近律:极端例子
在这里,我们看见由3个距离较近的黑点构成的一些线条,以竖直方向向右上倾斜。人们一般不会以另一种结构来看它,或就算以其他结构去看,也非常吃力——即由3个彼此分隔较远的黑点构成的线条,以竖直方向向左上倾斜。
相似律:当相似和不相似的物体放在一起时,我们总将相似的物体看作一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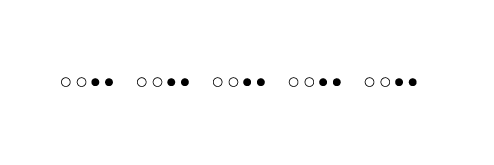
图 4 相似律:简单例子
相似因素实际上可以克服就近因素。在下面的左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四组距离较近的物体;在右边的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两组分布在各处但相似的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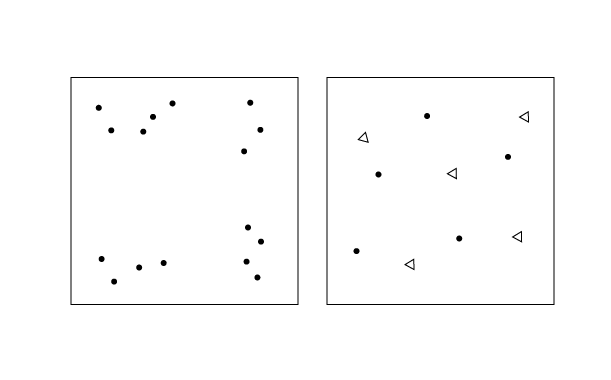
图 5 相似律:复杂例子
方向的连续律:在许多模式中,我们倾向于看见一些有内在连续性或方向性的线条,我们可据此在令人迷惑的背景中找出有意义的形状来,如平常所玩的“藏图”游戏。这样的线条或形状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格式塔”——内部具有连贯性或需求。例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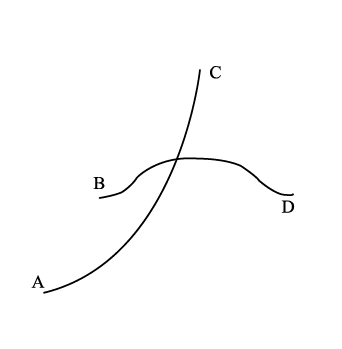
图 6 连续率:两条曲线呢,还是两个有尖角的图形?
我们只能强迫自己将其视为两个弯曲的、有尖角的图形,即AB和CD,但我们倾向于看到的是更为自然的格式塔形态,即两条相交的曲线AC和BD。连续因素可构成相当惊人的力量。考虑下列图案:

图 7 两个图案,它们一样吗?
再看下面,前两图合并在一起就成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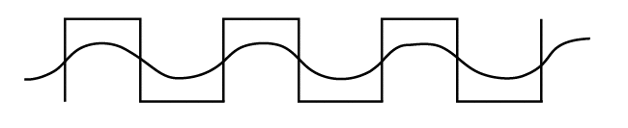
图 8 相同的图形,但就视觉上说,你能将其分开吗?
在合并的图中,几乎不可能再看出原来的图形,因为连续的波纹线已控制整个图形。
求简律:相关的英文词是“怀孕”(pregnancy),但该词并不能传达韦特海默的意思,因为他所要表达的是“看见最简单形状的倾向”。正如自然法则使肥皂泡采取最简单的可能形状一样,思维也倾向于在复杂的模式中看见最简单的格式塔。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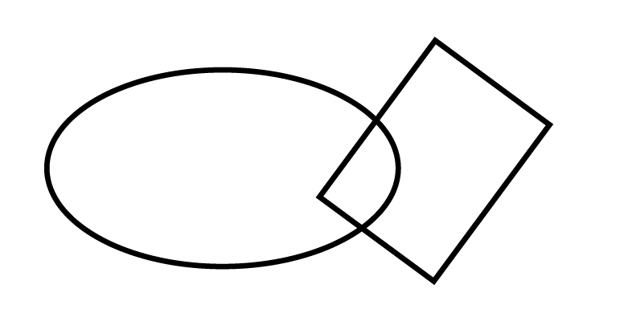
图 9 求简律:我们只看见最简单的可能性形状
该图可解释为一个被直角切去右边的椭圆相接于一个被弧形切除一角的长方形。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到的要简单得多,即一整个椭圆和一整个长方形互相重叠,仅此而已。
闭合律:这是求简律的一个特别并且重要的案例。我们在看一个熟悉或连贯性的模式时,如果某个部分失去了,我们则会把它加上去,并以最简单和最优秀的格式塔对它进行感知。比如,在下图中,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它看作一颗五星,而不是五个构成此图的V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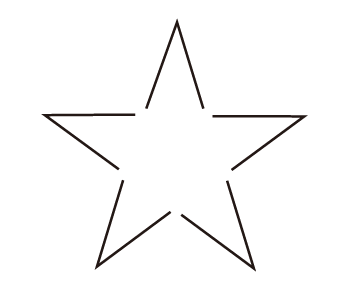
图 10 闭合律:我们把缺失的部分补上去
20世纪2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注意到,侍者能轻易记住尚未付款的客户的账单细节,而一旦付过之后,他就会立马忘记。这使他想到,这是记忆和动机领域的一个闭合案例。只要交易没完成,它就没有闭合,因而可以引起张力,保持记忆。一旦闭合完成,张力即消除,记忆也就消失了。
卢因的学生,一位名叫布鲁玛·塞加尼克(Bluma Zeigarnik)的俄国心理学家,用一非常著名的实验测试了老师的推想。她给志愿者分配些简单任务——做泥人、解决算术问题等一连串工作——很快又打断他们,不使其完成任务。几个小时后,她要求他们回忆所做的工作,结果发现,他们能清楚地记忆尚未完成的任务,而已经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记忆效果要低很多。这个效应被称为“塞加尼克效应”。
图形-背景感知:注意某物时,我们一般不注意或很少注意它的背景。我们看的是一张脸,不是脸后的房间或风景。1915年,古丁根大学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Edgar Rubin)深入探讨了图形-背景现象,即大脑将注意力集中于有意义的图案而忽略其他数据的能力。他使用许多测试图案,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鲁宾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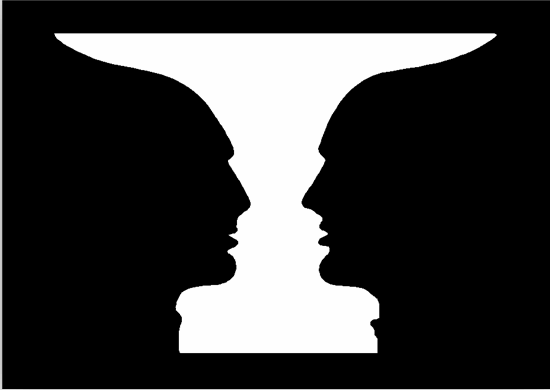
图 11 鲁宾瓶,是陶器还是剪影?
如果看到瓶子,你就看不到背景;如果看到背景——两个人脸的剪影——你就看不见瓶子。
尺寸衡定律:一个已知尺寸的物体,拿到远处去的话,会给视网膜留下较小的图像,但我们感知到的却是它的真实大小。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联想主义者认为,我们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格式塔学者却发现这个解释过于简单。对雏鸡加以训练,使它们只啄大颗饲料。在该习惯完全形成之后,把较大颗的饲料放在远处,使其看起来要小于近处的较小颗粒,小鸡仍毫不犹豫地直奔远处的大颗饲料。对11个月大的女婴进行训练(通过奖励办法),使她在两个并列的盒子中选择较大的盒子。把较大的盒子移至足够远的地方,使大盒子看起来很小,可婴儿还是选择远处的那只大盒子。
我们感到,远处的物体与它们在近处同样大小,因为大脑用相互关系——如邻近的已知物体或可提供远景的特性——的办法组织了这些数据。图12中的两图摘自最近的感知教科书,可对此进行说明。

图 12 远景可提供物体大小的线索
在左图中,远处的人与他身边物体及与走道的相互关系可使我们将他视作与近处的人一样大小。然而,在视网膜上,远处那个人的图像却要小许多,如右图所示。
第四节 够不到的香蕉及其他难题
萨尔顿是一只雄性猩猩,它整个上午什么也没有吃,已经饿极了。饲养员领着它来到一个房间,天花板上吊着一串香蕉,但它够不到。萨尔顿朝着香蕉又蹿又跳,接着,它开始在屋子里打转,发出不满的吼声。在离香蕉不远的地上,它发现一根较短的木棍和一只很大的木箱,它拿起棍子,试图打下香蕉来,可依旧够不着。有一阵子,它来回跳个不停,极为愤怒,突然,它直奔箱子,把它拖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轻轻一跳就拿到了奖品。
几天之后再次实验,香蕉被挂得更高,而且不再有棍子。所不同的是,屋内有两只箱子,一只比另一只稍大一些。萨尔顿自认为明白该做什么,它把大箱子搬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蹲下来,似乎要跳起来。但它看看上面,并没有跳,因为香蕉挂得太高了。它下来,抓住小箱子,拖住它满屋子乱转,同时愤怒地吼叫着,踢打着墙壁。显然,它抓住第二只箱子,并没有想到要将其叠放在第一只箱子上面,只是拿它出气。
然而,它猛然停止叫喊,将较小的箱子直拖到另一只箱子一边,稍一用力,就将其放在大箱子之上,然后爬箱子,解决了香蕉难题。一直站在一边进行观察的沃尔夫冈·苛勒将这一切尽数记载下来,并表示了由衷的高兴。
在1914年至1920年间,苛勒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对猩猩的智力进行研究。苛勒的发现直接导引出格式塔心理学家对人类解决难题的类似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发现。
苛勒在与韦特海默进行完运动的错觉实验之后,于26岁时,受命为普鲁士科学院设在特里莱夫的猩猩研究站站长。特里莱夫是西班牙偏远的属地孔拉里岛的一部分。苛勒于1913年整装出海,万没想到的是,此后发生的世界大战和德国战后的混乱竟将他困在岛上长达6年之久。
在这期间,苛勒设立了许多不同的难题让猩猩解决。最简单的是绕道问题,猩猩得通过转弯抹角的路径以获取香蕉。复杂一些的是使用工具,即猩猩得使用工具才能获取挂在高处的香蕉。如棍子,猩猩可用它打下香蕉。再如梯子,它们可将它靠在墙上和箱子上。
有的猩猩需要较长时间才可看出箱子是用以获取香蕉的,有的猩猩总是做些徒劳无益的事情,如把箱子码在离香蕉很远的地方,或码得水平过差,待它爬上去时,箱子往往翻倒在地。另一些猩猩显然要聪明一些,做得也很出色。它们学会以更安全的方式码放箱子,即使要码放两只以上的箱子才能取到香蕉。雌猩猩格兰德甚至在需要时可使用4只箱子,虽然在码放它们时颇费周折。
猩猩似乎能时不时地突然在某个节骨眼儿上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苛勒解释说,这是猩猩在脑海里对形势的重塑。他将这种突然的发现叫作“感悟”。
苛勒证明感悟是可以诱发的。苛勒常把一只猩猩放在笼子里,再把香蕉放在笼子外面它够不到的地方。他在笼子里放一些棍子,猩猩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知道用棍子够取食物,但可能在突然之间,它会想到这一点。一个叫谢果的雌猩猩先用手尝试着抓取香蕉,半个小时后,它失去了信心,干脆躺了下来。但另外几只猩猩出现在笼外时,它一下子跳了起来,抓住一根棍子,猛地把香蕉拨到跟前。显然,其他猩猩接近食物对它起了促进作用,从而诱发出了她的感悟力。
苛勒还有一个对认知心理学意义重大的发现,那就是,感悟式学习不一定依靠奖励。当然,猩猩一直在寻找奖励,但其认知的结果并不是奖励带来的,因为它们在吃到食物之前就已解决了问题。
另一项重要的发现是,当动物得到某种感悟时,它们不仅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还能概括并把稍加改变的方法应用到其他不同的情形之中。按照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感悟式学习能进行“积极传递”。按照一般人的说法,猩猩已学会应付各项考试。
苛勒在1917年的专论中报告了自己的发现,在1921年又出版了《类人猿的智力》。他的专著使心理学界大受震动,苛勒的观察为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人类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铺好了道路。
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一位心理学家利用苛勒式方法对一些1岁半至4岁不等的孩子进行实验。在实验中,即使这些远未成熟的孩子,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要远远高于成熟的猩猩。
类似的实验还包括年龄更小的8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8~13个月不等。这些实验是稍晚的卡尔·登卡尔(Karl Duncker)做出的。登卡尔最重要的研究发生于1926年至1935年之间,主要研究成人受试者解决问题的能力。
登卡尔的其他主要研究方法是把受试者带入一个房间,里面堆满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请受试者完成一项任务,而这些东西里根本没有一样东西适合这项任务。该实验的目的是测试受试者在什么情况下能考虑常见的东西有其他的可能用途,又在什么情况下不能考虑到。
实验发现,解决问题者如果认定某物体具有专门用途,就很难看出它的其他用途。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一些最熟悉自己所从事行当的人往往最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一位专家看其手中的工具时,看到的是各个工具的专业用途。一个生手尽管可能出些不着边际的馊主意,但也往往能够提出极有创见的新方法。毫不奇怪,科学家们往往是在早年提出其最有创见和重要见解的。
第五节 学习
格式塔心理学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有关学习方面的研究。
好玩的是,第一份证明联想主义等学说存在严重不足的证据,是一只母鸡的思想。苛勒在特里莱夫岛时,曾对四只鸡进行过实验。他让其中两只鸡啄食散落在一张浅灰色纸板上的米粒,当发现其啄食另一张深灰色纸板上的米粒时即将其赶走。同时,让另外两只鸡接受相反的训练。大家都知道鸡特别傻,但经过400~600次实验之后,前两只鸡便只啄浅灰色纸板上的米粒,而后两只鸡也只啄深灰色纸板上的米粒。
接着,苛勒将两种情形互换一下,让鸡学会吃食的那张纸板的背景颜色保持不变,但将另一张纸的色调调换。对前两只鸡,调换成更浅的灰色,对后两只鸡,则换成更深的灰色。联想主义者可能得出预测,鸡认准了纸板的颜色,只会在原来的纸板上吃东西。但在70%的实验中,被训练在较浅纸板上吃东西的母鸡大多选择新的、颜色更浅的背景,学会在较深背景上吃食的母鸡则大多选择新的、颜色更深的背景。格式塔学说提供的答案是:动物所学的不是两种颜色,而是两种颜色之间的关系。
苛勒在一只猩猩和一个3岁幼童身上重复了这个实验。他们两个各得到两只箱子,一只是暗色,一只是亮色。当猩猩受试时,亮色箱子里放着食物;当孩子受试时,亮色箱子里面放着糖果。猩猩和孩子都知道亮色的箱子里有奖品,但此时苛勒拿走了暗色的箱子,各用一只比盛放奖品的箱子更亮的箱子替代之。这一次,他在两只箱子里都放了奖品,这样的话,除两只箱子的颜色不同外,没有其他的激励因素以供挑选。结果,猩猩和孩子通常选择的都是新的箱子,即更亮的箱子。
但苛勒的实验无一例外地证明,动物所学的不是两种颜色,而是两种颜色之间的关系。关系是感知、学习和记忆的关键。这个事实此前被排除在心理学之外,现在又由格式塔学者重新将其找了回来。
韦特海默、苛勒、考夫卡和他们的许多学生都对学习问题进行了探索,宣布该观点的许多功绩却大多归在考夫卡名下。这位害羞、自疑、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性格古怪,嗓门巨大,但当他坐在桌前编辑事实和学说时,却总是心旷神怡,游刃有余,文笔既有大师的气度,又尖刻泼辣。
考夫卡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什么值得注意的认知研究。然而,由于他的英语很好,1921年他接受《心理学快报》的邀请用英语讲解格式塔心理学。自此之后,考夫卡就成为整个运动的非正式代言人。考夫卡的两本书《思维的成长》和《格式塔心理学原理》让格式塔心理学研究发现和有关学习的思想广为人知。除此之外,考夫卡的理论也为记忆方面提出了一些有见解的思想。
第六节 失落与成功
在德国,如我们所见,格式塔心理学已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领导学派。在其3位创立者及其学生相继离开德国之后,格式塔心理学于30年代中期几乎销声匿迹,重心转向美国。考夫卡于1922年开始发表介绍性文章,之后,格式塔心理学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激起了相当的热情。
然而,当时的美国正在流行行为主义学说,行为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根本不给格式塔思想任何发展空间。而几十年之后,格式塔心理学得到了众多研究形式的强力确证。比如,对语言获取能力的研究证明,儿童被教授语法之前就会按照语法说话。行为主义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反感也遭到报复,考夫卡、苛勒和韦特海默均对行为主义学说不屑一顾,并将自己的学说视作唯一有效的理论。
到30年代末,格式塔心理学虽已在美国心理学界扎下根来,但仍是二流。然而,他们对心理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却远超出了其人数和位置的影响。
韦特海默热情但没有耐心,因而并不是个好老师。考夫卡枯燥无味且古板教条,却颇受其所教书的史密斯大学女生的青睐,他所著的百科全书式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对心理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苛勒尽管拥有德国人的古板,却是3个人中在传统学术圈子里混得最好的一个。他创立了一个心理学研究中心及一份奖学金,吸引来许多一流的博士生。苛勒于1958年退休,但一直积极从事研究工作,直到9年以后他年届80岁为止。退休以后,他得到了美国心理学界的最高颂扬,并被选为美国心理学学会主席。
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到20世纪中叶,尽管格式塔运动已失去地位并销声匿迹,但它的一些重要概念却渐渐汇入心理学的主流,迄今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格式塔心理学的基础教义,即整体——格式塔——重要于构成它的所有组件,并主宰我们的认知力,完全经受住了时间与实验的双重考验,在感知、解惑和记忆领域仍发挥着作用。
更重要的是,格式塔学者把意识和意义重新带入心理学,他们并没有对冯特的信徒或行为主义者的发现造成损毁,只是极大地扩大了科学心理学的范围和规模。如考夫卡所说:
我们并不是被迫从心理学和普遍意义的科学中废弃诸如意义和价值这些概念,相反,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概念以更全面地理解思维和这个世界。
1950年,已成为遥远流派的格式塔心理学慢慢失去了影响,对此,艾德温·波林用迄今仍无人超越的文笔对其命运小结如下:
学派可以没落,也可因成功而消亡。有时,盛极必衰……(格式塔心理学)开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但把它继续标榜为格式塔心理学已不再具有益处。格式塔心理学的巅峰已经过去,现在已是盛极而衰,销匿在心理学的海洋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