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人名逻辑的认识始于一个基本问题:词语的含义到底栖身何处?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即共有两个可能的栖身之处。一处是外部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单词的所指;另一处就是我们的头脑,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一个单词使用方法的理解。
语言是通往人类灵魂的一扇窗口,对于任何一个热衷于此观点的人来说,外部世界似乎只是一个希望渺茫的栖息地。举例来说,“猫”这个词所指称的是世界上所有猫的集合,无论是已经死去的还是即将出生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人能够了解所有的猫,死去的、活着的、即将出生的。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语言中还有许多词根本就没有对应的所指物,比如,独角兽、伊莉莎·杜利特尔以及复活节的兔子,但对于那些了解这类词的人来说,它们无疑是有意义的。此外,人们还可以用意思相去甚远的单词来指称世界上的同一个事物。就这一点而言,教科书上经常引用的例子就是“长庚星”和“启明星”,事实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名称所指称的都是那颗独一无二的金星。然而,对于那些天文盲以及无法了解它们所指的人来说,这两种称谓的意思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希腊也有一个有关两个单词指称同一事物但却不被人所知的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那位底比斯的国王俄狄浦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一个女人——伊俄卡斯忒,也是他的生母。正如我们常看到的那样,语义的细微差别可以导致同一事件的后果大相径庭。
与这种“词义即其所指称的全部事物的集合”的看法相对立的观点是,词义是某种描写(摹状),类似于字典中的定义,或者逻辑或概念符号的公式。数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有限的描写代表无限集合的显著模式。举例来说,“被2整除的自然数集合”,这仅仅由10个字组成的描写却归类出一个由无限多偶数组成的集合。不仅如此,数学还向我们展示了利用两种不同描写方法来归类同一组数字的方法,如偶数的另一种表述方法是:“包含0的自然数集合,且集合中所有数都可在0上加任意多次的2来获得。”回到语言上,利用这种数学方法,我们可以将猫的语义描写为:“一只小型驯化的哺乳动物,身上有柔软的皮毛、尖爪、尖耳朵,通常还会有一条毛茸茸的长尾巴,且被广泛地当作宠物饲养或用于捉老鼠。”
“含义”的两种意思有时也被分别称为“所指含义”(reference,外部世界中的一起事件或一组事件)和“概念含义”(sense,一种总结范式)。一个词的“概念含义”未必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所谓概念含义是对隐藏在一个单词背后的概念的理想化描述(ideal characterization),而对于该语言的个体使用者来说,他们对每个词的概念含义只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了解而已。不过,他们头脑中确实存在着某些概念,并能将这些概念与一个词语的概念含义相匹配,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应该算是了解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的。相比于猫的集合定义,具体指一只猫的定义更具优势,因为它可以被装进人们的头脑中。当然,无论哪种定义,作为一个了解词义的人,他起码得具备识别词语所指的基本能力。不过,至少在原则上,一个词的概念含义可以帮助人们挑选出它在外部世界中的所指物(referents)。以前面提到的猫的词义为例,人们只要找到一个具有小型、驯化、尖爪、尖耳朵特征的哺乳动物就可以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词的概念含义起着维持人们与该词的可能所指物之间的联系的作用,不管这个词的概念含义有多么数不胜数,或者多么远离人们日常的生活体验。
遗憾的是,由于不同类型词的概念含义与所指含义的分工相去甚远,因此,“含义究竟存在于外部世界还是人们的头脑中”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对于像“这个”、“那个”这样的词来说,在选择外部世界中的所指物时,它们本身的概念含义丝毫也派不上用场,因为它们对事物的指称方式完全取决于说话人使用它们的时间、地点和场所。逻辑学家们因此将这类词称为指示语(indexicals)。Indexicals这个单词来自拉丁语forefinger(食指),因为指示语的含义取决于人们所实际指向的东西。语言学家则将它们称为指别语(deictic),deictic一词来自含义相同的希腊词根,即指向(pointing)。属于这一类的词还有:这儿(here)、那儿(there)、你(you)、我(me)、现在(now)和那时(then)。
上述这类词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与此相反,语言中还有一些词语,当人们根据规则中的系统来支配它们的意思时,它们就指称那些人们意欲它们指称的事物。至少从理论上说,你大可不必走进外部世界去亲自观察到底什么是着陆、什么是议会成员、什么是美元、什么是美国公民,或者什么是“大富翁”游戏里的GO,因为它们的意思已经由游戏或系统中的规则精确地制定出来了。这类词有时被称为名义类(nominal kinds)——一种所指物的选定只能由人们对其命名的方式来决定的词语类型。
这样,我们就有三类区别并不十分明显的词类了:自然类(natural kinds),例如,猫、水、黄金;人工类(artifacts),例如,铅笔、燕麦片、粒子回旋加速器;专有名词类(proper names),例如,亚里士多德、保罗·麦卡特尼、芝加哥,等等。现在的问题是,在面对这三类实体时,人类的心智与外部世界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首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专有名字的情况。乍看起来,要想了解一个名字,人们首先要了解它的概念含义,而不只是它的所指含义。我们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耳闻目睹所有名字的所指物,因为众所周知,有些人的名字(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我们出生前的几千年就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有些情况下,意思不同的名字还可以指称同一个事物:这类例子不仅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长庚星与启明星,还包括塞缪尔·克莱门斯与马克·吐温、克拉克·肯特与超人、吹牛老爹(Puff Daddy)与吹·老爹(P.Diddy)。那么,存储在人们头脑中的那个名字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想必,它大概就像一个“限定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一种能区分出一个个体的特征描写。比如,“乔治·华盛顿”这个名字的意思特指“美国第一任总统”。有时,一个限定摹状词还会被某些个人或团体作为自己的个性称呼,比如那个曾经被誉为“王子”(Prince)的艺人。不过请注意,名字和限定摹状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伏尔泰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是神圣、罗马,也不是帝国;而格鲁乔语录中的“军事情报”的军事和情报根本就是两个自相矛盾的术语;还有那个抨击美国右翼势力组织的车尾贴标语:“道德多数派同盟既不道德也不代表多数。”上述这些隽语均提醒我们:名称与限定摹状词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差别。按照我们目前所提及的这个理论,一个名称的含义应是一个限定摹状词的缩写词形式,尽管像前面那些笑话所传达的那样,它未必包含于这个名称自身。
现在是该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独创理论(早期版本是由露丝·巴肯·马库斯[Ruth Barcan Marcus]提出来的)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该理论曾一度被普遍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哲学发现。它的建构基础来自于一些匪夷所思的思想实验。下面我将借用一个听起来略微合理的思想实验来介绍一下克里普克的理论,不过,它可不是哲学家精心炮制出的思想实验,而是出自底特律一个与克里普克理论同时代的电台节目主持人的遣词造句。
让我们从当前的假设,即名称是限定摹状词的缩略词形式开始我们的介绍。举例来说,保罗·麦卡特尼这个名字的含义可能类似于你在字典中查到的如下定义。
麦卡特尼,保罗(Paul McCartney,1942—),人名。英国音乐家,流行乐团披头士乐队(1960—1971)成员,与约翰·列侬合作谱写过许多著名歌曲,其中包括《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和《顺其自然》(Let It Be)(同:麦卡特尼、詹姆斯·保罗·麦卡特尼爵士)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现在我来介绍这个思想实验——它其实就是盛行于1969年秋,至今依旧真假难辨的关于保罗·麦卡特尼死讯的传闻。根据这个报道,1966年11月一个星期三的早上5点,麦卡特尼在与披头士乐队一起录音的过程中愤然离开,中途他让一个叫丽塔的女人搭了车,后来他们误闯红灯,结果麦卡特尼在一场可怕的车祸中丧生。事发当年,披头士乐队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保罗之死无疑意味着他们的名声和财富都将为泡影。为了挽回损失,他们招募了一个替身顶替保罗的位置(即保罗模仿秀大赛的获胜者,比利·希尔斯[Billy Shears]),并成功策划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这就是披头士当年突然终止巡回演出计划的原因(现场表演太容易泄露天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突然都蓄起了胡子(为了掩盖那个替身嘴唇上的一个疤痕)。正如人们对一起精心设计的阴谋所预期的那样,在歌曲和专辑封面上,他们刻意为阴谋论者们埋下了许多暗含玄机的线索。
在《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专辑封面上,披头士乐队站在一块墓地上,保罗的那把左撇子低音吉他被插花点缀着。在专辑的封底上,披头士乐队的所有成员都面向前方,唯独“保罗”一人背对着镜头。这张专辑中有一首歌,描写的是一个男人神情恍惚地坐在车里,而另一首歌则哀叹:“已经没有可以挽救他生命的回天之术了。”此外,在其他歌曲和专辑中,人们也能发现一些若隐若现的线索。比如,在那首《永远的草莓地》(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的结尾处,人们可以隐约听到约翰·列侬的歌声——“我安葬了保罗”;而当回放《革命9》(Revolution N0.9)时,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约翰在反复吟唱那句“给我点激情吧,你这死去的家伙”。他们的另一张专辑《艾比路》(Abbey Road)的封面为人们呈现的则是一个葬礼的画面,葬礼行列中,约翰扮演传教士的角色、林格是送葬者、乔治是掘墓人,而保罗的那个替身则光着脚板(意大利人就是这样埋葬死者的)。在该专辑的开场曲中,约翰为乐队的复兴而高声歌唱:“1+1+1=3,在一起,马上来我这里。”
假设传闻属实,正如逻辑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存在着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中,那个传闻“确实是”真的。现在让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前面提到的关于保罗·麦卡特尼的定义。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我们心目中的那个人,事实上已经不是披头士在1960—1971年期间的那个保罗·麦卡特尼了,当然,《生命中的一天》和《顺其自然》也就不是他写的了,而且他也不再是1997年被封爵的那个人了。所以,假如“保罗·麦卡特尼”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那个定义的话,那么,1942年出生于利物浦、1966年死于伦敦的那个人就不是保罗·麦卡特尼了。不过,这显然违背了人们的直觉。大多数人都会说,尽管发生了那场悲剧,定义中的那个人依然是麦卡特尼。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让我来扩展一下这个思想实验。还记得“披头士第5号成员”斯图尔特·苏利夫(Stuart Sutcliffe)吧,他于1961年离开了披头士,第二年死于不明原因,或者“据说如此”。与麦卡特尼一样,在许多歌迷心中,苏利夫也曾是个外表俊朗的低音吉他手,且被视为披头士乐队的化身(他首创了披头士乐队的名称、服装风格以及他们著名的发型)。这难道真是巧合吗?我个人认为这不可能。很显然,披头士乐队没有位置能同时容下苏利夫和麦卡特尼两人,否则,苏利夫是绝不可能离开当时正处于成功边缘的披头士乐队的。我想也许是麦卡特尼想了一个妥协的办法。这很有可能——也不难想象,即存在着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里,苏利夫私下仍为乐队效力,并以保罗的名义写歌、演奏低音吉他、演唱专辑中的歌曲,而保罗则不过是乐队中的一张漂亮脸蛋而已。当保罗死于车祸时,除了前台表演的那个人之外,什么都不必改变!现在再回头看前面的定义,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定义中的名字“保罗·麦卡特尼”指的是苏利夫,就是1971年前一直为披头士乐队效力、并与列侬合作谱写《生命中的一天》的那个人。不过,这还是有些不对头。即便结果证明苏利夫符合“麦卡特尼”的标准定义,但我们仍会觉得,这个名字并不真的指称他,而是指称1942年出生时被其父母命名为詹姆斯·保罗的那个人。
所有这一切让我想起了引言中遇到的与此同构的问题:那个隐藏于莎士比亚名下的剧本并非莎士比亚所著“事实”的阴谋问题。与“麦卡特尼”的定义一样,即使传闻是真的,人们直觉中的“莎士比亚”这个名字所指的仍然是那个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的人,而不是写了那些剧本的什么人。我们在引言中探讨的有关身份窃取的问题也是这样,即使你名字的定义遭到了篡改,你仍有权宣称,你的名字所指称的就是你本人。
不过,请你大可不必为此感到纠结,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传闻恰恰捕捉到了克里普克理论的精神实质。下面我来介绍几个克里普克本人采用的案例。以亚里士多德为例,尽管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但是,即使他当时决定做个木匠而不是老师,或假设他两岁就夭折了,我们仍然会认为,我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就是亚里士多德。再比如,很多人认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个名字所命名的是证明了“地球是圆的”的那个人,而“爱因斯坦”所命名的则是那个发明了原子弹的人。即使这些信念是错误的,但我们仍然会觉得,这些被误传的人名所指称的还是我们认定的那两人。同样,就西塞罗来说,很多人除了知道他是罗马的演说家之外,对于他的其他事情却一无所知。很显然,演说家并非只有西塞罗一人,可是,每当人们提起这个名字时,他们意欲指称的就是罗马的那个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古罗马时期的演说家。
基于上述情况,克里普克得出的结论如下:一个名称根本就不是一种缩略的描述,而是一个“固定指示语”(rigid designator)——一个指定在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中均相同的个体的术语。换句话说,一个名字所指称的就是一个个体,而这个个体必须具备以下特点,即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我们均能够理性地谈论他/她,而无须考虑关乎他/她的任何传记事实。事实上,在一个人的父母为其指定了某个名字的那一刻起,这个名字的所指就被固定了下来。随后,在这人的有生之年及其死后,人们会一直用这个名字指称他,这要归功于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给你讲一个关于一位伟大哲学家的故事,他的名字叫亚里士多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起描述(如“美国第一任总统”或“一只小型驯化的哺乳动物,身上有柔软的皮毛、尖爪、尖耳朵”),名字更接近于指示语(如“这个”、“你”等)。当我们知道一个名字时,便可以毫无疑虑地用它去指称一个人,而不用考虑对其都了解了些什么。
你会发现,就这些在可确认的时间里由一个命名者授予的专有名称来说,这个理论是很容易被接受的。问题是,其他两种词类——即自然类和人工类词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以自然类词为例,如“黄金”、“原子”、“水”和“鲸鱼”。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词都有一个定义,从“黄金”开始,“黄金”即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水”即H2O,“鲸鱼”即鲸目的几个家族。而且,科学家的任务正是设法发现这些词语的定义。
不过,就像我们通过“麦卡特尼”和“莎士比亚”的定义所了解到的那样,这种看似无害的观点却与人们某些强大的直觉发生着冲突。其中一种直觉源于我们对词语定义的观察。人们发现,现代科学对一个词的界定很可能与他们(包括科学家本人在内)对其所指的习惯看法不一致。举例来说,鲸鱼曾被认为是巨型鱼(曾经吞食过约拿的动物,古希伯来语称其为“大鱼”),但现在我们知道,鲸鱼是哺乳类动物,而绝不会是其他什么碰巧长得很大的鱼,比如“鲸鲨”。毫无疑问,当“鲸鲨”这个词被那些不懂科学者使用时,他们指称的与我们指称的肯定是完全相同的动物。同理,就“黄金”这个词的界定来说,古代炼金术士与20世纪物理学家会给出完全不同的描写,不过,无论定义的差别有多大,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谈论的是完全相同的物质。界定原子的物理学家也是如此,无论他们将原子定义为不可分裂还是可分裂的单位,原子就是原子,它们不会因为定义的不同而发生任何改变。
当我们对一种自然类的科学认识发生变化时,用于命名这一自然类的那个词并不会改变它的含义,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含义”与这些词的指称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原始指称物总会被人们的心智记住。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不同时代的科学家(或持不同理论的同一时代的科学家)根本就无法对同一事物进行探讨,而他们之间的分歧自然也无法消除。因此,代表一个自然类的词义与一个名字的含义是一样的,它并不是一种描述或定义,而是指向外部世界某个事物的“指针”。创世伊始,当某人意欲使用一个词来指称一类事物时,他便用这个词为这种物质或物体命了名,这个词也就因此获得了一种含义(比如,父母给孩子命名)。随后,出于同样的目的,人们将这个名称世代相传,比如,他们会说:“这东西叫作‘黄金’。”
当然,一个自然类术语的所指与第一个命名者指称的不可能是同一块黄金或同一个水坑里的水,就这一点来说,它与一个名字的所指就是父母当时命名的那个人是不同的。这并不是说那块黄金或者水坑被掩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自然类术语包含的是所有属于此“类”的物质——一般来说,就是那些具有某种共同隐藏特征的物质或者具有某些可能会被科学发现的共同本质的物质。对于当初那个命名者及其随后的沿用者们来说,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那种共同的本质是什么,但却能感觉到其存在,也或许那是一种用某种复杂方法统计学公式才能捕捉到的特性。举例来说,普特南就曾承认,他不知道“榆树”与“山毛榉”之间有什么区别。不过,他知道这两个单词并不是同义词——对他来说,尽管他自己不能区分这两种树木,但他知道专家们能做到,这就足够了。普特南认为,词语就像商品和服务,它们属于一个社会内部劳动分工的产物:我们往往要仰仗专家去区分含义上的不同,而无须自己亲自去做。
借助当今著名的思想实验,普特南为我们阐释了自然类术语并无定义的观点。设想遥远的天边有一颗行星,它是地球的一个复制品。生活在那里的人不仅和我们长得一样,就连思维方式也一样。他们的生活环境也与我们差不多,甚至他们说的语言也很接近英语。但唯独有一件事情是不同的,那就是,被当地人称为“水”的液体,它的化学成分并不是H2O,而是一种由长而复杂的化学方程式组成的化合物,其方程式可以缩写为XYZ。在这个孪生地球上,XYZ是一种维系生命的无色液体,它可以解渴、灭火、从天而降、溢满湖泊和海洋。这意味着,我们地球人头脑中存储的有关水的知识与孪生地球人大脑中所存储的知识是一样的——孪生地球人天生具有与人类相同的大脑,而且他们的大脑体验与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大脑体验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要一杯水(碰巧是H2O)喝的情景也适合他们(碰巧是XYZ)。
现在,假设词语的含义是存储在头脑中的,那么地球上“水”的词义和孪生地球上“水”的词义应该是一样的。然而,这种推理与多数人(参与过这个问题思考的人)的直觉是相悖的——他们一致认为,“水”这个词在两个行星上的意思不同。我估计,假如有一天我们的化学家们有机会造访这个孪生地球并对他们的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物质进行检验,这种差别会被渲染得更大——他们会说:“孪生地球人不喝水,他们喝XYZ!”即使这只是想象,但我们还是觉得,水是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所使用的同音同形异义词,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知情。基于这个孪生地球的故事和上面提到的榆树-专家的例子,普特南总结说:“爱怎么给词义下定义就怎么下吧,反正‘意思’就是不在人的头脑中!”
你可能会反驳:“好吧,‘水’这类词倒是说得过去,但是,那些复杂概念系统的自然类词语,比如动物种类词的情况也会是这样吗?假如一个人连猫是一种动物都不知道的话,那么他就不算知道‘猫’这个词的词义,这一点总归可以肯定的吧?”但是请注意,假设科学家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惊人事实:“猫”原本指的就是达雷克(dalek)[7],一个来自虚构星球Skaro的Kaled族人的变种人。Kaled族人是个一心想要征服并控制宇宙的冷酷民族,他们穿着自己巧妙设计的机械盔甲,将自己伪装成动物,横行于宇宙之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能仅仅因为“猫”被定义为一种带毛的动物,就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猫吗?或者,我们能说,与我们先前的信仰相反,猫就不是动物了吗?假如我们在其他星球上发现了“喵喵”叫的小型毛茸茸的动物,那又该怎么办呢?换句话说,我们还能谈论“它们”吗?如果你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能”,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猫是动物”,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不能”的话,那么就等于说,你和普特南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与名称一样,自然类术语也是“固定指示语”(rigid designators)。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词类了——人工类词。你起码可以说,铅笔是手工艺品,即书写工具是“铅笔”这个词的部分含义。但现在让我们假设,科学家又发现了一个更令人叹为观止的事实:铅笔是个生物体。当我们把它切开并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时,我们会发现,它们有神经、血管和脏器。不过,有谁曾见过它们产卵生小铅笔呢?又有谁见证过一支婴儿铅笔的成长过程呢?(普特南说:“说实话,这确实很奇怪,很多这类有机体的外表都有个商标,不过,也许它们本来就是智能生物,那些标签只不过是它们用于伪装的外形而已。”)如果你承认它们还是铅笔的话(反对“科学家已经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铅笔’这种东西”的说法),那么就等于已经承认,即使“铅笔是人造工具”,它也不是“铅笔”含义的一部分。
当然,词义的某部分一定在人们的头脑中。我们不仅需要某些东西来区分哪些人了解一个词的词义、哪些人不了解,而且,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所看到的,两个不同的名称可以指向外部世界中的同一个事物(启明星与长庚星;伊俄卡斯特与母亲),但由于说话者在知识状况上的差别,它们的含义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如此说来,普特南的否定(ain't)断言(他所说的“反正含义‘就是不在’头脑中”)应该改成选择(either-or)断言:“词义要么不决定其所指(词语所代表的事物),要么就不在人的头脑当中。”当今,就含义的切分方法而言,许多哲学家采取了与普特南略有不同的方式,他们主张“含义”有“两种”意思,即狭义和广义。“狭义”以定义、概念结构或者常规范式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英语中的“水”和孪生地球人所使用的英语中的“水”具有相同的狭义)。“广义”指向外部世界中的事物,它基于说话者头脑之外的许多事情:说话者从哪些人那里学来这些词、又是从哪里学到的这些词;如果你能追溯到足够遥远的年代,那么,当初的造词者们在使用这些词的时候,他们所指向的又是些什么(英语中的“水”和孪生地球人所使用的英语中的“水”因此也就有了不同的广义),等等。
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可以无视头脑中的狭义与将外部世界带入自己头脑中的广义之间的区别呢?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用担心语言背后的思想会错误地刻画我们所使用的词语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除了哲学家与阴谋论者的思想实验之外,人们头脑中的含义与外部世界中的含义往往指称的都是同样的事物。我们的心智与世界如此协调,以致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所想与我们认为的我们的所想完全一致。当然,这并不排除例外的存在。确实有误识身份的情况,比如,用“哥伦布”指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居民。也确实有重新划定界限的情况,比如,“海豚”被动物学家重新归类为鲸的一种。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当“圣·尼古拉斯”(Saint Nicholas)这个固定指示语演变成“圣诞老人”(Santa Claus)时,这期间一定发生了不小的错误。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并不需要担心这些匹配上的错误。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远远没有我们的哲学所幻想出来的那么多。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某些法则,只不过我们的词语习得官能对它们熟视无睹而已。事实上,宇宙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看起来像水、喝起来像水,但却是由XYZ构成的物质;不存在不仅长得像猫,而且行动也像猫的达雷克;更不存在什么看起来像铅笔的生物体、杀害亲生父亲并迎娶亲生母亲的悲惨巧合、披头士乐队瞒天过海的骗局,等等。幸亏有这些来自世界运转方式的约束法则,我们才不至于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被这些奇思妙想愚弄。
然而,仅凭世界本身的合作性来建立人类与世界间的可靠联系还远远不够,人们还必须对词语受制于外界事物这一心照不宣的事实深信不疑。不仅如此,人们还必须相信与自己同一个语言社团的其他人,不管是健在的还是已故的,也都对这个事实深信不疑。在那些思想实验面前,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才使人们坚定地认为,词语是锁定在某些人或事物上的,即使知道那些人和事物与他们想象中的相去甚远,他们的信念也不会动摇。也正是因为这个信念,人们得以学会了那些无法亲自验证的词语,因为他们坚信,总是有人可以去验证它们的。也许正是人类这种直觉,让那条词语习得链从词语的始创者开始从未中断过,无论那个起点离我们有多么遥远,无论它的历史有多么悠久,也无论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发生过多么大的变化。一想到每次谈及亚里士多德,我们就要穿越一条源远流长的语言链,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被这个名字所指称的那个人,这实在有些令人既惊奇又毛骨悚然。事实上,每当你用一个词指称某一事物时,就等于将自己系在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时-空线上的一端,而它会将你连线到那个第一次看着这个事物(比如,一颗星星、一个生物、一种物质)并决定用这个词为它命名的人。
请注意,词语所连接的是人与外界事物,而不是人与自己所“认为”的外界事物。这种联系方式并不只是在人们直觉地处理稀奇古怪的思想实验时才会有所表现,即使没有侦破欺诈和身份盗窃案件等诸如此类的实际应用问题,科学和法律上的重大难题同样会引发我们对词语与概念指称的实质问题的深思。
以“物种”为例,在生物学的发展史上,这一术语的含义问题应该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以及当今的创世论者中),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每个物种都可以被一组必要的特征所定义,具体来说,人们认为金枪鱼、山雀、响尾蛇等生物都有一个准确定义。然而,当生物进化论思想出现后,这种观念却令他们陷入一种难堪的困境,因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生物进化势必衍生出非驴非马的中间类生物。按照实在论(essentialist)的理论体系,恐龙具有恐龙的本质,它不可能进化成鸟,这就好比三角形不可能演变成正方形一样。达尔文对概念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于,他一改过去用一组固定特征来定义一类物种的方法,将物种名称处理成生物种群的指示语(pointer,一种固定指示语)。也就是说,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一个种群的成员特征是可以发生改变的,不仅如此,该种群后代的特征分布也会随着时间逐渐发生变化。作为一种固定指示语,物种名称可以直接指向一个巨大的物种谱系树中的某个分支,其中包括一开始就用这个标签命名的成员、它们的同种物种、它们的部分祖先以及部分与它们足够类似的其他物种。
对许多外行来说,学术界近来对名称本质论战的煽动性并不不亚于人们对进化论本身的论战。触发这场名称论战的原因是,人类确实在太阳系中发现了类似于XYZ的水、机器人猫、有生命的铅笔等想象世界中的物质。以冥王星为例,冥王星曾被认为是一颗行星——或者我应该说,冥王星的前身是颗行星。而结果证明,冥王星并不同于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等8大行星。与首次发现冥王星的天文学家当时的认识正相反,冥王星只是一颗很小的冰球,比月球还要小,它沿太阳系不稳定的轨道缓缓运行,与周围其他同样绕轨道运行的小冰球并无多大差别。为解决冥王星的归属问题,2006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委任的一个专家小组特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整个世界都对这场论战的最终结果异常关注。如果天文学家们将其贬出9大行星,那么他们同时也会令数以百万计的卧室手机和课堂挂图变得一文不值。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激起一代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慨,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背着9大行星的顺口溜长大的,比如,My very eager mother just served us nine pizzas(我那非常热心的妈妈为我们准备了9个匹萨)或者Many vile earthlings make jam sandwiches under newspaper piles(很多卑鄙小人在报纸堆下面做三明治果酱)。[8]不幸的是,那些能够用来将冥王星留在9大行星俱乐部里的相关规则同时也会将各式各样的小行星、人造地球卫星以及冰球等混入这个行星俱乐部中。而不划定界限,这个定义就无法保证“行星”这个词仅仅指称9大传统天体。
客观地说,这其实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科学论战,而是一场关于词语逻辑的克里普克-普特南式的游戏大战。在多数人心目中,如同其他名字一样,“行星”这个词就是个固定指示语。在我们的语言社团中,它指称的是9大行星构成的集合——在这个例子中,它指向的并不是一个命名时刻(因为冥王星是在1930年被发现的,而“行星”一词在这之前就被使用了),而是一种过去的命名行为,在我们首次接触“行星”这个词时,这种行为就已经完成了。因此,尽管有关它的知识(我们设法给予这个词的概念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人们仍然会觉得这个名字依旧指称那些处于他们集体记忆当中的事物。针对这一问题,天文学家们面临的困境是,他们既需要一个能够科学地涵盖一个连贯类型的技术术语(比如,化学中H2O的对等词,或者生物学中一个物种的名字),又不忍心放弃这个语言中固有的单词。不过,为了成就科学的严谨,最终他们还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将冥王星从一颗行星的身份降级成了“矮行星”,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这一固定指示语的直觉。
关心名称所指问题的不仅有科学界,法律体系同样关心人们会利用词义来指称什么的问题。要做到公正,法律就必须划清事前人们用于支配一种行为的潜台词与事后陪审团用于判断那个行为的潜台词之间的界限。这就要求指称类型、行为的法律术语务必与法律定义完全一致。然而,能够进入到人们思想和行为当中的概念往往都是自然类和人工类的概念。而这两类概念又都是些固定指示词,就这一点而言,法律希望用定义取代概念的企图在原则上是行不通的。在《不良行为和犯罪心理》(Bad Acts and Guilty Minds)一书中,利奥·卡茨曾经借助如下例子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在非洲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政府曾经通过了一项《巫术法案》(Witchcraft Suppression Act),该法案对“巫术”进行了详细的定义。不幸的是,法案的起草者们并不谙熟当地的风俗,他们将“巫术”定义得一塌糊涂,甚至将某些原本用于探测巫术的宗教仪式也定义成了巫术。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一个被告人确确实实施了巫术,但他实施的却不是法令上所“定义”的巫术,面对这样的被告,法官该如何为他定罪呢?假定一个单词的含义就是它的定义的话,那么这个被告应被判无罪。但假定“巫术”之类的术语是一种固定指示语的话,那么它所指称的就应该是立法者在起草法令时为其规定的行为,即使他们当时对这一行为的特征作出的表述并不准确。许多美国人都知道,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也有一个与此平行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几十年来,我们的立法者和法院一直都没能就“淫秽”一词的定义达成一致。1964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曾给出过一个模棱两可的定义:“我见到了就知道它是不是淫秽的了。”
此外,克里普克还从命名语义学中得出另一个怪诞的结论,这个结论出现在其题为《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的论著中。至少从康德开始,思想家们就已经区分两种类型的知识了。一种是先验知识(priori knowledge),先验(在事实发生之前)知识即人们常说的躺在扶手椅上就可以获得的知识——通过神的启示、内省、先天思想,或者通过逻辑和数学推导获得的知识。另一种是后验知识(posteriori knowledge),后验(在事实发生之后)知识即只有通过走入世界亲身观察才能获得的知识。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估计是杜撰的,在中世纪的一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试图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推导一匹马的嘴里到底有几颗牙齿。讨论过程中,一个年少妄为的学者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找来一匹马,观察一下它的嘴巴,然后数一数它的牙齿,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么。然而,这个建议一经提出,在座的学者们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对哲学家来说,“先验知识”意味着很多东西,其中之一便是一组“必然”(necessary)事实——即只能如此的事实,因此,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是成立的。与此相反,后验知识是关于“偶发”(contingent)事实的知识。它们取决于人们对世界的体验,体验不同,获得的后验知识也会不同。毕竟,仅凭一组公理和规则,人们是很难对某些事情作出合理推断的,尤其对那些由原始太阳系的斗转星移、变幻莫测的方式所决定的事情,或者由某个碰巧在地球惨遭彗星撞击时出现的物种所引发的事情。相反,假如有人能够对这类事情作出合理的推断,那么,鉴于这种推断所使用的词语的逻辑蕴含(比如,所有“单身汉都未婚”),或者这个推理蕴含的数学真理的普遍永恒本质,人们便会认为,这类事情“必然”是这个样子的。
康德还设法对第三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知识是先验的,但它不只是语义的结果——知识是对我们所了解的物质世界的实际描述。康德认为欧几里得几何公理是对空间特征的描述,尽管这些公理是通过数学推导出来的,而不是利用卷尺和水准仪测量出来的,但它们却是人们生来就有的先验知识。今天,几乎没有人再接受康德的这种先验时空观了,因为至少现代物理学已经向世人证明,空间并不是欧几里得几何。
克里普克则对另一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这种可能性是多数哲学家连想都不曾想到的:知识不仅是后验的(在事实之后被发现的),而且是必然的。举例来说,长庚星和启明星指称的是同一颗星体(金星),这个事实的发现是后验的。但一经发现,这一知识就成为必然真理——没有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中的长庚星和启明星指称两颗不同的星体(尽管长庚星和启明星本身可以被“称作”不同的事物——但克里普克所说的是我们用这两个词语所指称的事物,而不是这两个词语本身)。同样的道理,如果科学家们对水是H2O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水就“必定是”H2O——如果某种事物不是H2O,那么,根据我们所说的“水”的含义,它最初就不是水(还记得我们不承认孪生地球上的物质是水的那个例子吧)。同样,黄金就“必定是”原子序数79的物质(如果这碰巧就是它的原子序数),热就“必定是”分子运动(假设它实际上就是分子运动),等等。
与中世纪的学者座谈马的牙齿数量不同,上述这些观点都不是学者们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中的想入非非。最终被人们接受的必然事实取决于科学实验的发现。这里,克里普克真正想要澄清的实际上是一个逻辑问题,即人们在使用专有名称和自然类名称时,他们所致力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承诺的问题。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研究表明,人们所致力的是逻辑必然真理的某一类型(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什么样的先验)。克里普克的后验必然性主张修正了人们对真理的种类以及认识方式的理解——所有这一切均源于我们对名称使用的直觉。
可以肯定的是,站在这个距离上观察含义的概念,我们会嗅到悖论的气息。当我用一组单词来表达什么时——当我指称亚里士多德、半人马座阿尔法星、水、偶数、2050年出生的第一个婴儿,或者如果保罗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时,我到底是在做什么呢?仅仅激发一些神经元或是动动嘴,我就可以和一位已故的哲人或者一个遥远的天体发生联系,这着实令人振奋不已。至少在这些例子中,我们瞥见了说话者与处于词语习得链另一端的含义之间的关系。每当人们反思是什么将我们与语言的所指连接在一起时,思绪便开始不停地盘旋于种种实体之上:水(无论宇宙中哪里的水)、抽象实体的无穷集合、一个尚未出生的人(一个特定的人,而不是其他数十亿人中的任意一个已出生的人),或者一个没有现实存在,但却遵循着一定自然规律的平行宇宙等。尽管这些实体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的身体也没有用于感知它们的器官,但是,一条精致的语义链却将它们与人类巧妙地连接在了一起。
正如哲学家科林·麦金(Colin McGinn)所说,含义似乎“能使思想超越生疏之界:带领我们穿梭于亘古亘今,畅游天涯海角,它肆意穿越现实,但始终不会偏离自己的正确轨道”。如此说来,难怪有那么多不同文化中的名门贵族们都相信,词语具有神奇的魔力(正如我们将要在有关发誓赌愿那章中所要看到的那样);也难怪一本福音书会如此开宗明义地写道:“太初有道(语言),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对此,麦金作出了一个更加淡定的解释:含义的问题,就像哲学上许多其他未解之谜一样,可能永远都会被笼罩在迷雾中,因为正是这个问题将人类的常识推向了那些原本不属于它的概念王国。
新词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假如一个名字的含义真的可以将我们与一个原始的命名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事件呢?在为一个概念标签时,人们又是如何构思这个新的声音符号的呢?什么样的无名概念才会被人们认定是值得拥有一个标签的呢?一个名称的传播链不仅能使其广泛流传于一个语言社团当中,而且还能使它跨越时空、世代相传,这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在本章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依次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事实上,在那些令人类感到新奇的领域中,人类最初创造的词语也是独具匠心的,它们往往具备下面一些特点:(1)知识含量惊人;(2)废话含量惊人。一些涉及词源的信息还会被人们添枝增叶。我这里就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它们曾通过电子邮件被人们郑重其事地广泛传播过,该邮件的主题是“献给琐事爱好者:短语的由来”: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床垫是由绳索固定在床架上的。当你拉绳子时床垫就会收紧,这样,床睡上去就会更加坚固。这就是“Goodnight, sleep tight”(晚安,睡个好觉)的出处。
4000年前,巴比伦有这样一个风俗,婚礼后的一个月内,新娘的父亲要为女婿提供“米德”(Mead),女婿能喝多少就得提供多少。米德是一种蜂蜜酒,当时巴比伦的历法基于月亮的圆缺(阴历),因此,这一新婚阶段便被称为“蜜月”(honey month),或者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度蜜月”(honeymoon)。
在古代英国,除非得到国王的许可,否则人们是不可以擅自过性生活的(除非你属于皇室家族)。假如有人想要生孩子,他们必须先得到国王的应允,一旦应允,国王会给他们一个招牌,日后做爱时,他们必须将那块招牌挂在门上。牌子上写着F.U.C.K.(Fornication Under Consent of the King[国王应允下的私通])。现在你知道fuck这个词的来历了吧。
这些传言让人们想起了词源学(Etymology)。Etymology一词源自拉丁语etus-(被吞噬)、-mal-(坏的)以及-logy(研究)。它的字面意思是“对那些不容易吞噬的事物的研究”。只要查一下字典,上面那些荒诞的词语典故很容易就能被戳穿。这说明学者们已经掌握了不少英语单词的真正起源,这些词源有时会追溯到原始的造词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追溯到原始词根,或者几百或上千年以前的毗邻语言。一般来说,真正的词源远不如民间传说那般丰富多彩、栩栩如生。Tight(紧)的词源含义是“稳定和安全”,例如,sit tight(坐稳);honeymoon(蜜月)暗指一种隐喻性的甜蜜,这种甜蜜会像月亮一样逐渐隐退;fuck(性交)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意为“有节奏的舒张与收缩”或者“插入”。顺便说一下,testify(作证)并非源自古罗马男子以自己睾丸(testicles)发誓的习惯;shit也不是Ship High in Transit(航海过程中升高货舱甲板)的首字母缩略词,Ship High in Transit是航运货物上的警告语,提醒水手在航海过程中切记升高货舱甲板以防海水浸湿货舱中的肥料、产生沼气,从而引起货舱爆炸。不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时,真正的词语典故也非常妙趣横生,那绝不是一个编造者能臆造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人们使用的最常见的造词法就是对旧词或词的部分组件(词素)进行重组。每种语言都拥有一系列组合操作程序,该程序以一套可预测的方式不断地创造着新词。以英语为例,通过在动词后面添加词缀-able,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指称该行为的可能性或难易程度的形容词,例如,learnable(可学的)、fixable(可固定的)、downloadable(可下载的)等。将两个名称合并起来,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合成词,以此来指称以第二个名称为核心语的事物,例如,ink cartridge(墨盒)、lampshade(灯罩)、tea strainer(滤茶器),等等。一般来说,这类新词的产生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说话者在不经意间便可以将它们创造出来,听话者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懂它们的所指,例如,outdoorsiness(户外商品)、uncorkable(不能用软木塞的)、pinkness(粉红色),等等。
假如这些就是全部的构词法,那么我们的语言将远比现在乏味得多,不过,这倒是能让语言更加循规蹈矩一些。如果真是这样,理查德·莱德勒也就没有理由再质疑:婴儿(infants)是否犯步兵罪(infantry)、人道主义者吃什么、婴儿油是什么制成的以及其他那些修辞性问题了(参见本书第1章中提到的那些修辞)。英语(以及其他语言)之所以变得如此疯狂,就是因为词语具有一种累积特性的习惯,而且这种特性无法通过它们赖以生成的规则逻辑进行预测。举例来说,transmission(传输)不仅指一种传递行为,还指一种汽车零件(变速器);一句言辞如果是unprintable(不宜刊印的),并不是因为它会弄坏印刷机,而是因为它是淫秽的;arrow-head(箭头)是箭的“头”,而redhead(红发女郎)却指一个红色头发的女人。不仅如此,我们有很多类似的head(头),比如,egghead(秃头)指称知识分子、blackhead(黑头)指称粉刺、pothead(瘾君子)指称大量吸食大麻的人,还有Deadhead,一个指称“感恩而死”乐队的粉丝的专属名词。造成这种疯狂的原因之一是,由一条规则生成的词语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有记录的词形当中,并同时将使用者赋予它的特殊含义也累加给这个词形(就像上面提到的“传输”的例子那样)。造成这种疯狂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规则为所生产出来的新词留下了语义细节上的空缺,而这些空缺的填充必须建立在逐词逐句的基础上(就像上面提到的由head[头]构成的那些合成词那样)。
除了像上面提到的加词缀法和合成法等系统构词法以外,还有许多即兴的造词法。在任意一个新词表中,比如字典出版商一年一度公布的“年度词汇表”,都不难发现这些造词技巧的蛛丝马迹。以收录在《麦克米伦英语词典》(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2005年度词汇表”为例,这个词汇表实际上是一本造词法的指南大全:
● 加前缀法(Prefixing):de+shopping意为“出于仅仅使用一次便要求退货的意图而购买的商品”。
● 加后缀法(Suffixing):Who+vian意为“英国科幻系列剧《神秘博士》的粉丝”。
● 词性转换(Changing the part of speech),比如,将一个名称或形容词变成动词:supersize(超大型快餐)意为“提供一个特大号的版本”。
● 合成词(Compounding):gripesite意为“一个专门警告消费者伪劣产品和服务的网站”。
● 外来语(Borrowing from another language):wiki(维基百科),意为“用户可以对文本进行集体编辑的一个网站”(wiki源自夏威夷语,意为“迅速”)。
● 首字母缩略词(Acronyms):ICE意为“In Case of Emergency(以防万一),联系电话存储在手机的通讯录里”。
● 截词(Truncation):fanfic(同人小说),意为“由粉丝而非原创作家创作的新故事,故事人物、情景均来自一部电影、一本书或一个电视节目”。
● 混成词(Portmanteau,由一个词的开头部分和另一词的结尾部分混合而成):spim(spam+I.M.)意为“通过即时通信(Instant Messaging)发送的垃圾广告”。
● 逆构词(Back-formation,对一个词的错误分析并对其中一个成分再利用):preheritance意为“在世的父母为子女提供经济援助而不必以遗产的方式将财产留给子女(子女无须缴纳遗产税)”。
● 暗喻(Metaphor):zombie(行尸走肉),意为“个人电脑在遭到病毒攻击后,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病毒驱动发送垃圾邮件”。
● 换喻(Metonym):“7/7”意为“恐怖爆炸事件”,源自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爆炸事件。
此列表中的40个单词中,只有一个词的词根是全新的:dooced,意为“由于在博客中发布了某事而被解雇的”。这个词根诞生的故事几乎超出任何一个民俗词语学家的想象力。它的创造者是一个因在自己的博客上粘贴了某个消息而失业的人,其博客地址是www.dooce.com。她用自创的、惯用的错别字dooce(代替doode)为自己的博客命名。而doode这个词是她刻意杜撰出来的,她用这个词的发音来记录她的一个冲浪朋友在发dude(纨绔子弟)的元音时夸张的发声。
这个滑稽的故事引发了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人们到底是怎样酝酿出新词根的呢?那些与其他多数新词的发音不同的词根,不仅发音独特,从词根的构成上来看,它们也不是对现有词语和语素的再利用,它们是一套原创的元音和辅音的组合体。毫无疑问,dooce这种来源的词根毕竟是少数(即人们为了描写某种时尚的发音而杜撰出来一个错别字,然后用此错别字为自己的博客命名,dooce因其博客而得名)。当然,绝大多数词根并非来自博客的起名人。
一种最常见的新词根来源就是拟声词(onomatopoeia),即发音类似于其所指的声音的单词,例如,呼噜声、叮当声、呕吐、昏迷、低音扬声器以及高频扬声器。但拟声词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它只适用于有噪声的事物,而且就连一个听起来十分相似的事物,拟声词也未必派得上用场。与事物发声的自然输出相比,拟声词更多地受语音模式的管辖,就像我们在下面的漫画中看到的不同语言中动物的叫声也不同。

Robotman?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比纯粹拟声构词更方便的是声音象征(sound symbolism),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词的发音仅仅“提醒”人们这个声音所指的某个方面。长词可能会被用于指称较大或较粗糙的事物,节奏不连贯的词用于锋利或迅猛的东西,用口腔或喉咙深处发音的单词用于很久以前或在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件。例如,比较this(这儿)与that(那儿)、near(近处)与far(远处)、here(这里)与there(那里),等等。图5-1中的两个平面图是一个声学或发音语音学的暗喻,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中,它们都可以被发现。实验证明,人类对模式非常敏感,即使是虚构的词语模式也不例外。下面请你猜一猜,这两个图形哪一个可能是malooma、哪个是tak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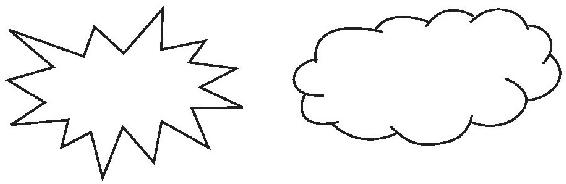
图5-1 语音学的暗喻
大多数人都会赞成左边的是takata,因为尖状图形提醒人们尖尖的声音;右边的是malooma,因为雾状的形状会让人们想起缥缈的声音。假如我告诉你,汉语中的“重”(heavy)和“轻”(light)读平调或降调,现在你来猜猜,哪个读作qīng、哪个读作zhòng?我想,大多数英语使用者都能猜得出来,那就是qīng对应着light, zhòng对应着heavy,反之不然。人们已不止几十次地“发现”过这种声音象征,而且,每一次的发现者们都声称,这一发现证明了索绪尔倡导的“任意性音意结合原则”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些发现并不能真正驳倒索绪尔的观点,因为,你永远也无法从一个词的词义中预测出它的发音,你也同样无法从它的发音中预测出词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人们创造或改造一个新词时,声音象征一定是构成他们创作灵感的一部分。
语言中还存在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象声词(phonesthesia),拟声和声音象征是它的种子。在这类词语中,整个词类共享着同一个微弱的语音和一个微妙的含义。举例来说,英语中,许多单词都有一个sn-音,这个音与鼻子有关,可能是因为当你发这个音时,几乎可以感受到鼻子的皱起。这类词包括有关鼻子本身的单词。
snout(鼻子);类似鼻子的器具,如snorkel(潜水通气管)、snoot(聚光镜头筒,引导射光的锥状体);与鼻子有关的指称行为和事件的词语,如sneeze(打喷嚏)、sniff(嗅)、sniffle(鼻塞)、snivel(流鼻涕)、snore(打鼾)、snort(喷出)、snot(鼻涕)、snuff(鼻烟)、Snuffleupagus(动画人物,长鼻先生);还有往鼻子下面看,表示歧视某人的词语,如snarky(尖刻的)、sneer(冷笑)、snicker(窃笑)、snide(暗讽的)、snippy(暴躁的)、snob(势利)、snook(轻蔑)、snooty(傲慢的)、snotty(下贱的)以及snub(冷落)。
sn-还与迅速、秘密或贪得无厌的行为有联系,比如,snack(快餐)、snag(意外障碍)、snap(猛咬)、snare(陷阱)、snatch(抢夺)、sneak(告密者)、snip(剪断)、snitch(顺手牵羊)、snog(爱抚)以及snoop(窥探,或者它是一个表示多管闲事的单词吗)。
不过,这其中的依据远不如sn-与鼻子有关的词的依据那样显而易见。也许人们在sn-的发音中能够嗅到一丝速度和柔和的味道吧,但这种解释似乎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嫌疑,而且只能应用于英语的音节首辅音(onset)。象声词更有可能是从一些出于各种原因联合在一起的相似词语的一个共同核心中发展出来的。有些词可能是声音象征的产物。有些可能是某个形态规则的化石标本,这个形态规则既有可能是活跃于本族语言初期的一条构词规则,也有可能是活跃于外族语言(这些象声词的起源族的语言)中的一条规则。还有一些词的出现可能纯属偶然,由于一种语言的语音结构只允许这么多数量的元音和辅音的组合,因此它们就被随意地安排在同一个语音空间里了。但是,一旦这些词语发现它们正在并肩携手时,便会利用人类记忆所特有的物以类聚的联系本能吸引或生成新成员。在《词与规则》中,我曾经向读者介绍过“物以类聚”这种记忆特征是如何催生出一族相似的不规则动词的,比如,sing-sang(唱)、ring-rang(按铃)、drink-drank(饮)以及wind-wound(缠绕)、find-found(发现)、grind-ground(磨碎),等等。这里有一些其他辅音连缀,你可以对它们语音的象征情况作出自己的判断:
cl-黏着体或者相连的一对平面:clad(覆盖的)、clam(钳子)、clamp(夹紧)、clan(氏族)、clap(鼓掌)、clasp(扣住)、clave(劈开)、cleat(夹板)、cleave(裂开)、cleft(崩裂)、clench(握紧)、clinch(钳住对手)、cling(附着)、clip(夹牢)、clique(小团体)、cloak(斗篷)、clod(土块)、clog(阻塞)、close(亲密的)、clot(凝块)、cloven(劈开)、club(俱乐部)、clump(集群)、cluster(丛)、clutch(抓紧)。
gl-光线发射:glare(眩光)、glass(玻璃)、glaze(光滑面)、gleam(闪烁)、glimmer(闪光)、glimpse(一瞥)、glint(闪亮)、glisten(闪耀)、glitter(闪烁)、gloaming(黄昏)、gloss(光彩)、glow(发光)。
j-突然运动:jab(戳刺)、jag(狂欢)、jagged(起伏)、jam(挤进)、jangle(吵架)、jarring(冲突)、jerk(痉挛)、jibe(转帆)、jig(抖动)、jigger(阻止)、jiggle(轻摇)、jimmy(撬开)、jingle(发出叮当声)、jitter(振动)、jockey(移动)、jog(轻推)、jostle(推挤)、jot(匆匆记下)、jounce(颠簸)、judder(颤抖)、juggle(变戏法)、jumble(混乱)、jump(暴涨)、jut(突出)。
-le小物体、小孔、小斑点的集合体:bubble(泡沫)、crinkle(条子泡泡纱)、crumble(面包屑)、dabble(蘸)、dapple(斑点)、freckle(雀斑)、mottle(色斑)、pebble(卵石)、pimple(丘疹)、riddle(谜语)、ripple(波纹)、rubble(瓦砾)、ruffle(皱褶)、spangle(亮晶晶的小东西)、speckle(斑纹)、sprinkle(洒)、stubble(须茬)、wrinkle(皱纹)。
一些拟声、声音象征、象声词的组合还催生出一系列空洞的词语,在本书引言的结尾部分,我曾列举过这些言之无物的词语。
当孩子们对词语突发奇想时,象声词便在他们的心中复苏了。作家劳埃德·布朗曾经给我讲过他女儿琳达的一些发明:
水哗哗啦啦地(drindling)流进了下水道。
一只老鼠沿着踢脚线飞快地窜过(scuttered)。
我那时正和那群男孩子们摸爬滚打(scrumbling)着呢。
我要用(面包)蘸(sloop up)肉汁。
为什么奶奶的脸皱皱巴巴(crimpled)的呢?
用手摇晃灯泡的时候,它为什么会发出细小的“咝咝”声(ringle)呢?
有趣的是,象声词还为比较语言学提出了一个可爱的难题:在世界各种语言中,为什么butterfly(蝴蝶)很少分享同一个词根呢?以西欧的语言为例,我们发现德语中的蝴蝶是schmetterling、荷兰语是vlinder、丹麦语是somerfugl、法语是papillon、西班牙语是mariposa、意大利语是farfalla、葡萄牙语是borboleta。令人费解的是,这些语言中的几乎所有其他类的词语都不规则地共享着某些词根。举例来说,英语的cat(猫)在上面提到的各种语言中分别为katze、kat、kat、chat、gato、gatto、gato。不难看出,butterfly这个词在世界各种语言中都是独创的,这个词往往会有一个叠音,最常见的是b、p、l或者f的叠音,就像希伯来语中的parpar、意大利语中的farfalla、巴布亚语中的fefe-fefe所表现的那样。就好像人们期望这些单词可以振翅高飞一样!当然,并不是“蝴蝶”的所有名字都是象声词,我们也发现了暗指蝴蝶特征的名称,这些特征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虚构的。在英语中,蝴蝶被描写成一种黄油色翅膀的两翼昆虫,或者是吃黄油的昆虫,或者排泄物像黄油一样的昆虫。民间词源学认为butterfly是flutter-by(飘过)的首音误置词(spoonerism),这种解释尽管很有吸引力,但遗憾的是,那不是真的。为什么各民族文化不愿意共享这些隐喻和典故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无从得知,不过,我倒很喜欢语言学家哈吉·罗斯(Haj Ross)的遐想:
始于一只前途未卜的毛毛虫,最终却以一对美丽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翅膀完成了蛹变成蝶的全过程,加之人们意识中无法忘怀的翩翩舞姿,蝴蝶所呈现给世界各个文化群体的是一种独特而强大的概念/意象。各种文化均将蝴蝶尊奉为旋乾转坤的完美象征,几乎没有哪个民族情愿接受其他民族赋予这个神话般造物的充满诗意的名字。每种语言都在寻找自己的隽言妙语来赞美蝴蝶的一生所带给人们的绝妙启迪。
近几十年来,象声词在那些一夜成名的英语词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
bling(锦衣珠宝)、bonker(疯狂)、bungee(蹦极)、crufty dongle(混沌电子狗)、dweeb(白痴)、frob(小物品)、glitzy(炫目的)、glom(一瞥)、gonzo(疯狂的)、grunge(蹩脚货)、gunk humongous(一大堆黏状物)、kluge(异机种系统)、mosh(狂舞)、nerd(呆子)、skuzzy(小型计算机接口)、skank(卑鄙小人)、snarf(狼吞虎咽)以及wonk(书呆子),等等。
当然,这些单词远非“蝴蝶”那样抒情。当象声词的松散联系被应用到较长的语言组合中时,它们还将成为品牌命名的一种不可忽视的资源。过去,公司常常以下面一些方法来为自己的品牌命名:公司创始人的名字(福特、爱迪生、西屋电器等)、表达公司之庞大的主题词(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等)、代表新技术的混合词(例如,微软、傻瓜相机、宝丽来自动显影电影设备等)、公司意欲传达的比喻或换喻(例如,黑斑羚、新港、公主、开拓者、反叛者等)。如今,它们正在寻求用人造的拉丁和希腊新词来传达自己产品的某种难以言表的好品质。这些人造词语由词语片段构成,而这些词语片段则是一些被认为可以传达某种品质、无须亲自体验便可以被感知的语素。Griffy(格里菲),这个名字令读者与动画家的困惑(第二自我)产生了共鸣。Acura(阿库拉,本田的一款车型)——准确的?尖锐的?这些含义与轿车品牌又有什么关系呢?Verizon(威瑞森通信)——一个名副其实的新视野吗?它是否意味着良好的电话服务将一去不复返了呢?Viagra(伟哥)——男性雄风?充满活力?充满生机?我们是否应该将其设想为令一个男子每次射精都瀑布般一泻千里呢?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当属美国菲利普·莫里斯母公司(以万宝路香烟闻名)的更名——Altria(奥驰亚集团),这大概是为了转变该公司曾向一些见利忘义的地区和国家出售让人上瘾的致癌物质的丑陋形象吧。

Zippy-Bill Griffith.King Features Syndicate.
未命名,还是无以为名
现在我们对新词的语音命名从何而来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难题就是,究竟哪些含义需要命名呢?换言之,命名的动因是什么呢?
常言道:“需求是发明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这句老生常谈为我们眼下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有人可能会想,新单词应该被用于填补词语的空缺:一个人人都想表达,但却没有现成贴切的词语可以表达的概念。人们只要偶然听到某个专有名词,如摄影、滑板运动、街舞以及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术语便会认为,总会有人提供新词来满足交际上的需求。例如,上一代的大多数人对现如今普通计算机用户使用的命令几乎闻所未闻——打开调制解调器、重启、运行随机存取存储器、上传、打开浏览器,等等。在声称男女平等的时代,假如没有“女士”这个词,那怎么能行?
不过,请别忘了,我们还有另一句谚语:“假如所有希望都能变成骏马,那叫花子也就有坐骑了”(If wishes were horses, beggars would ride)。语言中的许多空缺甚至拒绝被填充。我们在引言中已经遇到过两个这样的例子:一个是指称21世纪头10年的词,另一个是形容未婚异性恋的同居伴侣的词。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拒绝填补空缺的例子。比如,一个用于替代he(他)或she(她)的性别中立的第三人称代词——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曾先后提出过60种建议(例如,na、shehe、thon、herm,等等),但没有一种得以采纳。再如,指称一个成年子女的术语;指称子女配偶双亲的一个集体名词(例如,意地绪语中的machetunim);指称一个你学了100次也记不住的事实的术语;指称在火车上或在机场休息室里一个坐在你旁边一直冲着手机大吼大叫的笨蛋的名词;指称堆积在车轮后面并落了车库一地棕色的、令人恶心的雪块的词语;指称黎明时分憋了一肚子的尿液让你无法继续睡觉,而你又困得实在不想起来上厕所的术语,等等。
英语中如此之多的词语空白甚至催生出一种幽默类型。喜剧演员里奇·霍尔(Rich Hall)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词sniglet(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意为“本应存在,但实际却不存在的一个单词”,请看下面一些例子。
elbonics,名词。两个人在电影院暗争一个扶手的行为。
peppie,名词。一家豪华餐厅的服务员,他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随处看看顾客是否需要胡椒粉。
furbling,动词。在机场或银行,即使没有人在排队,还是沿着绳索隔出来迷宫般的通道前行的人。
phonesia,名词。折腾半天拨打电话号码,结果在接通对方的时候,却忘了要和谁通话。
不过,这些sniglet(本应存在,却不存在的单词)并不是首创。在它们之前,我们还有liffs(苏格兰一个小镇的名字)。1983年,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以《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著称)和电视制片人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出版了《Liff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f)一书,这本书是基于以下的观察著成的:“在生活中(实际上是在苏格兰的小镇Liff中),存在着成百上千的词语空缺,比如,描写某些共同体验、情感、情景,甚至那些广为人知的物体的词语。与此同时,却又到处充斥着无所事事的闲置词语,它们不过偶然出现在路标上用来指示地点而已。”于是,亚当斯和劳埃德决定将那些指称人迹罕至之地的地名用于为那些没人命名过的体验加标签,请看下面这些单词。
sconser,名词。指称一个人一边和人聊天,一边环顾四周,伺机寻找自己更感兴趣的人。
lamlash,名词。指称酒店梳妆台上放置的、令人乏味的信息文件夹。
shoeburyness,名词。指称当你坐在一个还留着别人体温的座位上时的那种难以名状的不适感。
hextable,名词。指称在某人的收藏中发现的、让你立刻就能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能跟他们一起外出的记录。
《词语逃兵》(Word Fugitives)是语言专家芭芭拉·沃拉芙(Barbara Wallraff)所著的一本关于娱乐造词的历史的书,也是她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中的同名专栏集,沃拉芙一反《词语逃兵》专著的表述方式,在专栏中,她要求读者们提交一份词语空缺表,然后其他人来设法填补这些空缺。
形容你在对自己的孩子说话时,意识到你的语气听起来很像你自己的父母的词语:déjà vieux、mamamorphosis、mnemomic、patterfamilias、vox pop、na-gativism、parent-riloquism。
形容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你本应该介绍两个人,但却记不起其中一个人的名字的词语:whomnesia、persona non data、nomenclutchur、notworking、mumbleduction、intro-ducking。
形容辩论结束三个小时后才想起来的一个机敏的反击:hindser、stairwit、retrotort、afterism。
形容那种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瞬间困惑,即当手机来电铃响,但谁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机在响的词语:conphonesion、phonundrum、ringchronicity、ringxiety、fauxcellarm、pandephonium。
《华盛顿邮报》的“风格邀请赛”专栏偶尔要求读者通过改变一个现成词的字母的方式来填补词语的空缺。
sarchasm,名词。辛辣讽刺的作者与百思不得其解的读者间的鸿沟。
hipatitis,名词。终端服务器冷却。
Dopeler effect,名词。当一些愚蠢的想法突然而至时,你会倾向于认为它们很精明。
Beelzebug,名词。凌晨三点钟,化身蚊子的撒旦闯入你的卧室,你又无法将它赶走。
此外,还有下面这个经常在电子邮箱中流传的题为“增加你的犹太词语”的词汇表。
yidentify,动词。尽管一些名人的名字为圣约翰、柯蒂斯、戴维斯或泰勒,但人们仍然能够识别出他们的种族本源。
mishpochamarks,名词。在亲吻了所有叔叔、阿姨、表兄、表妹后,脸上留下的口红和化妆品的痕迹。
santa-shmanta,名词。给犹太儿童的解释:为什么在其他各国都在庆祝圣诞时,他们却要庆祝光明节。
meinstein,名词。我的儿子,真正的天才。
尽管这些词多少给人们带来一丝望梅止渴般的快感,但这种以娱乐方式打造出来的词语绝大多数都不会成为语言中的永久成员。它们也很少会像deshopping(出于使用一次便要求退货的意图而购买商品者),或者preheritance(在世的父母为子女提供经济援助而不必以遗产的方式将财产留给他们)那样被“年度词语”征集。我在引言中曾经提到过,美国方言协会每年都会选出一些最引人注目、最有用、最可能流行的新词。一项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年度词的跟踪调查表明,社会专家们对流行词的预测水平几乎可以和小报灵通人士持平。有些词是针对政客的冷嘲热讽,随着政客的淡出而变得黯然失色,比如,to newt(纽特)和to gingrich(金里奇)。另一些以某个可爱的语素构成的新词,就像从人们记忆中逐渐淡出的那些曾令人激动一时的相关事件一样渐行渐远,举例来说,-razzi指一个咄咄逼人的追捕者,这个词缀流行于1997年,即戴安娜王妃因躲避狗仔队(paparazzi)的追踪而不幸遭遇车祸身亡那一年;drive-by大约流行于1996年,即比尔·克林顿反对drive-by deliveries(即美国妇产医院在新生儿出生24小时后就不再对母子负责的惯例),这个词是从drive-by shootings(飞车射击)衍生来的。还有一些包含了一项发明的错误名称的新词:notebook PC(笔记本电脑),在日常交流中,人们仍然用laptops称呼它、s-mail,随着它的来源snail mail(蜗牛邮件)的黯然失色而渐渐被人遗忘、W3,人们错误地以为World Wide Web(全球资讯网)会简化成这种形式、information super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这个词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有关(指刊登有关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相关消息的网站)、Infobahn(德语:信息高速公路),等等。
事实上,新词的命运是一个不解之谜。填补了词语的空缺并不能保证它们可以流传下来;也不能保证它们具备另外两个卖点特征:简洁性和透明性。说WWW所需的时间要比说World Wide Web的时间还要长。然而,无论我们反复多少次地发这9个音节,它就是抵制被更短一点的音节,如triple-dub、wuh-wuh-wuh和sextuple-u所替代。
就透明性而言,面对start up(启动)和restart(重启,这两个术语用于操作系统的菜单)这两个言简意赅动词的挑战,新动词boot up(启动)和reboot(重启)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尽管事实上没有多少人知道boot(引导、踢)暗指的是什么。Boot(引导、踢)并不是“对着你的电脑猛踢一脚”的意思,在我做博士研究的那个年代,它指的是“计算机技术中生代时期电脑的开启方式”。那个时代的微型电脑简直就是一张白板,它甚至不能从磁带或磁盘上读取自己的操作系统。你得将程序和数据按字节逐个输入,为此,你还得在一个前端面板上安装一堆转换开关,字节中的每一个二进制位表示为1或0,这些1和0的组合构成程序指令或者数据块。即使对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生来说,这也过于单调乏味了,为了简单起见,你也可以装配一个只有几个字节的短小程序,给出计算机所需的一些信息,然后用穿孔纸带输入计算机即可。那些字节随后会合成一个略大一些的程序,告诉计算机怎样加载磁带上剩余部分包含的操作系统。纸带前端的小程序被称为“引导装入程序”(bootstrap loader),这是因为它的自动载入功能会让人们想起那句老话lift yourself up by your bootstraps(凭自己的力量重新振作起来)。这整个过程被称为“启动”(booting up)你的电脑。也许你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民俗词源学的杜撰,就像“国王应允的私通”(FUCK)那样,不过,我确实见证了那个时代,我可以发誓,这个词就是这么流行起来的。
艾伦·梅特卡夫(Alan Metcalfe),美国方言协会前董事长,《预测新单词》(Predicting New Words)的作者,曾经对为什么有些词得以广泛流行,而另一些词却销声匿迹这种现象做过解释。他用FUDGE这个缩略词总结了自己的看法:F代表频率(Frequency)、U代表不要太惹眼(Unobtrusiveness)、D代表使用者和使用情景的多样性(Diversity of users and situations)、G代表其他形式和含义的生成性(Generation of other forms and meanings)、E代表概念的耐久性(Endurance of the concept)。这虽然是个良好的开端,但实际上,它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所有词语均源自一个始创者,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的频率(F)和使用者的多样性(D)均始于1。不过在流通过程中,一些词的使用频率和多样性得到不断的提升和扩展,问题是,这种现象是个事实,而这一事实正是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本身,它并不是成因,因此,它不能用来自我解释。相同的循环解释也威胁到了梅特卡夫提出的新词形(一词多义)的生成性(G),例如,blockbuster(轰动)从指称一个大炸弹引申到指某种商业性的巨大成功。事实上,越是高产词,越容易一词多义(参见第2章),因此,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一个词语的成功会使这个词变成更好的新词义的生成者,而不是像梅特卡夫所说的,一个词的生成能力决定着它的成功。同样,概念的耐久性(E)也不是对一个词的生存境况的合理预测。尽管现在我们很少有机会谈论cabooses(守车)、flappers(苍蝇拍)、zoot suits(左特套服)和Cold War(冷战),但如果需要的话,这些词就在那里,它们随时恭候人们的召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梅特卡夫的“不要太惹眼”(U),事实上,它是给娱乐造词者以及“年度词语”的裁决者们的一句言简意赅的提醒,即绝大多数招摇过市的词最终都会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真正的赢家却波澜不惊地融入了语言的大潮。当然,前面提到的sniglets、liffs以及word fugitives中的大多数词都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这注定了它们终将被抛弃的命运。还有那些由诙谐的记者们有感而发所创造出来的妙语,尽管它们曾一度令“年度词语”的评判者们眼前一亮,但其中的大多数还是未能逃脱被淘汰的厄运。举例来说,Brown-out形容糟糕的紧急情况处理,它让人想起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那位联邦应急管理局局长;flee-ancée指称一个珍妮弗·威尔班克斯式的逃跑新娘,珍妮弗·威尔班克斯(Jennifer Wilbanks)曾在2005年一夜成名。幽默作家吉利特·伯吉斯(Gelett Burgess,1866—1951)1907年创造的blurb和bromide这两个词的运气还算不错,可是alibosh(公然的谎言)、quisty(耐用但不漂亮)、cowcat(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的人)和skyscrimble(八卦)就没那么幸运了。
即使有人甘愿使出浑身解数来传播一个新词,以此来填补某些词语的空缺,但老百姓还未必愿意领这个情。2000年,概念艺术家米勒杜斯·美尼塔斯(Miltos Manetos)注意到,在产品设计学中,英语缺少一个形容高科技审美的词,比如,“新苹果第三代MP3播放器真的X”以及一个指称由科技驱动的艺术媒体流派(例如,视频艺术、电脑绘图、数字动画)的词语,如“我们的美术馆展示了X派新艺术家的作品”。美尼塔斯希望找到一个既可以做形容词又可以做名词的词来填补这一空缺。本着他正在命名的那场艺术运动的精神,他特意聘请了品牌推广公司Lexicon Branding(就是那家设计了奔腾、赛扬、起亚远航、美国磁通公司和雪佛兰阿雷罗品牌名称的公司),希望该公司的计算机算法和从事语言研究的员工能为他提供一些候选词。在随后得到的候选词名单里,米勒杜斯选中了其中的neen这个词,neen在希腊语中的意思为“现在”。在纽约一个大型艺术馆中举行的一次发布会上,米勒杜斯隆重地推出了这个词,与会者包括新闻记者、批评家以及一个包括我在内的评论家组。我当时的预测是,这个词不大可能流行,因为它是个错误的象声词,它的共鸣过于倾向sn-音词或者像小孩子奚落人时发出的nyah-nyah和neener-neener。不幸的是,我的预测后来被证实是对的(只要谷歌一下neen就能验证这一点),事实上,作出这样的预测并不难,因为任何过于惹眼的新词最终都逃不脱被淘汰的厄运。
尽管如此,也不是每一个新词最终都会被摒弃,因为有些新词非常诙谐且自我。英语最近接纳了podcast(播客)这个新词,意为“下载到数字音乐播放器的音频节目”,它是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和broadcast(广播)的双关语;另外还有blog(博客),即Web log(网络日志),blog利用的是blob(难以名状的一团)和bog(沼泽)的无定形态(amorphousness),并以20世纪70年代校园俚语的风格对一个词音节进行了漫不经心的切分,如shroom(mushroom,蘑菇)、strawb(strawberry,草莓)、burb(suburb,郊区)和rents(parents,父母)。加拿大人将一加元硬币戏称为loonies(潜鸟),是对硬币背面的“潜鸟”的一种嘲讽。当二加元硬币进入流通时,它立即被戏称为toonie。数十年前,英语中有Yuppie(雅皮士),指专门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人,后来又衍生了hippie(嬉皮士)、Yippie(雅皮士)和preppy(预科生);还有couch potato(成天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懒虫)、palimony(分居抚养费)、qwerty(标准的传统键盘);当然,还有那个最愚蠢的spam(垃圾邮件)。这也算不上什么新生事物。Soap opera(肥皂剧)发明于20世纪30年代;hot dog(热狗)于19世纪90年代出自一个校园里对热狗所含原料的恶搞;gerrymander(改变选举区)则更早,它发明于1812年。动词razz(冷笑)和名词raspberry(咂舌声,舌头伸出发出粗鲁的噪声)并不是拟声词。它们从伦敦腔的押韵俚语中炮制出来,这种词的发音特点是,用一个短语代替一个单词,该短语与这个词相谐音,并且押韵的部分被省略掉了。比如,用loaf(面包)代替head(头,head → loaf of bread → loaf),或用apples(苹果)代替stairs(楼梯,stairs→apples and pears→apples)。按照相同的逻辑,如果我告诉你raspberry是raspberry tart的缩略语,你应该就能想象出raspberry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了。
尽管这些诙谐的发明偶尔会取得成功,但在指出“不要太惹眼”是新词能够成功留存于语言的常见条件时,梅特卡夫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某种东西的存在。然而,这种东西并不是“不惹眼”本身,而是一种能够满足词语的认知要求的能力。并不是所有在我们心里一闪而过的东西都有词义所需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对于一个可命名的概念来说,它通常会指称一类有序的事物,或者是一起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定规则可循的事件。此外,与专有名词不同,一个可命名的概念还必须是类属的(generic),而不能是个别的(particular)。举例来说,新通用名词latte-drinker(拿铁饮用者),指的是一类通常喝拿铁的人群(比方说,见过世面的城市青年),而不是指称某个此刻正在喝拿铁的人。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下面的句子中,“拿铁饮用者”可以毫无矛盾地被使用:“除了并不真的喝拿铁外,克雷格是个彻头彻尾的拿铁饮用者。”(但你却不能说:“除了并不真的喝拿铁外,克雷格从哪种意义上说都喝拿铁。”)词语往往用于描写有机整体(如“兔子”,而不是“未分离的兔子身体”)、稳定的品质(如“绿色”,而不是“2020年之前是绿色,之后是蓝色”)、自然种类、由一次状态改变或目标改变而终结的事件、具有某种功能的产品;也用于描写由显著因、果、手段或方式的行动。词语是供那些在我们所断言的事件中发挥作用的参与者使用,而不是供断言本身所使用的。因此,一个句子可以有真假之分,而词却没有。
鉴于词语的以上特性,充满趣味的新词往往顾此失彼——注重趣味性却忽略了精确性,它的趣味性并不是构词精巧所致,而是由于构造者对所命名的事物的评论,换言之,它实际上并不是在给事物命名,而是在对事物进行主观评价。以典型的年终新词列表为例,egosurfing(自我搜索)、celanthropist(名人慈善家)、infomania(过分沉迷于检查电子邮件和短信)、security mom(一个特别关注恐怖主义活动的选民)、ubersexual(一个不仅阳刚而且敏感,具有社会意识的异性恋男子)、greenwashing(一种意欲让公司看起来有很强环保意识的公共姿态)。这些词确实是符合社会潮流的新闻报道,你几乎可以感觉到这些造词者用胳膊肘轻轻地碰着你说:“看啊!互联网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性别角色、高科技、恐怖主义、环保意识正在变革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那些站在自己立场上的sniglets(本该有却没有)以及其他相关词语的造词者们,他们其实是在说“你不讨厌……”、“那不太傻了么……”或者“你有没有注意到……?”事实上,通过把这些瞬间的评价打包进一个词里,这些造词者们所做的就是对自己的评价进行再评价。他们总是说:“这种现象如此普遍、如此容易识别,它实在值得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词语!”我认为,这些造词者对词语心理学和俏皮话的非法利用才是造成这类新词幽默诙谐的真正原因。不幸的是,这也正是他们创造的新词无法留存在语言中的原因所在,他们同时也搞砸了这些词。假如你在没人排队的情况下,沿着银行的隔道线自行排队走向窗口;或假如在公交车上,你坐在了一个还留着别人体温的座位上,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愚蠢,不过,人们谈及这些情景的机会毕竟比评论觉得自己有多傻的机会还要少得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sniglets都用于描述错误和愚蠢的行为(比如,purpitation意为“从杂货店的货架上拿下来东西,当不想要的时候,把它随手放在其他摆货区”),对于做荒唐事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慰藉,但对于这些词来说,它们却很难成为由一个标准动词划分的事件类型。
退一步说,即便掌握了所有这些知识——构成工具、词语空缺、联觉音语境以及词语的概念要求,我们仍然无法预测一个新词什么时候会选择一个词根。余下的不解之谜将引导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来认识文化与社会,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得先回到史蒂夫之谜的那个话题上。
引爆流行的神秘力量
史蒂夫和其他婴儿名字的兴衰史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名称来说,仅凭悦耳的声音和一个可命名的概念还不足以达到流行的目的,这之外一定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命名一个孩子应该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为一种语言增添新词语的最简单的例子。父母可以随意选择语音,社团也会尊重他们的选择。即便如此,给婴儿命名还是暗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决定着一个单词的流行趋势,也许还能解释为什么有些词能够成功流行起来,而其他词却没这么幸运。
在某些方面,命名一个孩子与创造其他词语是有区别的。我们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本应存在却不存在的人名(比如,一个可怜的孩子,他的父母一直就没能抽空为他取名);我们也不会拒绝接受一对父母为他们的孩子选择的名字,只不过偶尔会给那孩子取个昵称而已。大多数时候,父母在给孩子取名时,会从常见的名字中挑选一个,他们一般不会临时杜撰。但因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是人类最纯粹、最民主的行为,而且有关婴儿名字的数据精确又丰富(美国社会安全管理局保留着一个自19世纪80年代起至今的全美人名数据信息库),这些名字为人们了解词语流行趋势提供了一个信息宝藏。
一个人不一定要叫那个名字才会了解这个名字的兴衰史。假如仅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大多数人也能预测出而不只是猜测出她的大致年龄。一个叫埃德娜、埃塞尔或贝莎的人,一般会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苏珊、南希或者黛布拉可能是一个处于生育期的少妇;詹妮弗、阿曼达或者希瑟应该是个30多岁的年轻女性;伊莎贝拉、麦迪逊或奥利维亚应该是个孩子。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猜她的年龄》(Guess Her Age)的文章,因为女孩名字的变化比男孩的更快:罗伯特、大卫、迈克尔、威廉、约翰、詹姆斯等名字始终都有人在用。不过,即便就男性的名字来说,如果让你猜测伊桑、克拉伦斯、杰森,当然还有史蒂夫的年龄,猜中的概率也会比投飞镖的中标率要高。当然,名字也并不都有流行周期——在许多社会中,婴儿必须以圣人或祖先的名字来命名,而且许多家长仍旧想方设法用世系味道浓重的名字为他们的儿子取名;而相比于儿子,女儿名字中的宗亲味道则略微淡一些。不过,不管怎么说,名字的使用情况总会有一些波动,而且在20世纪时,西方国家的这种波动率呈迅速攀升的趋势。
和我父母一样,大多数父母都不记得在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前,他们是否因为曾听过哪个婴儿的名字,于是就给自己的孩子也取了那个名字。他们往往会说,他们曾有一个最喜欢的亲人或心目中的人物;或者他们会说,他们只是喜欢那个名字的悦耳声音。但当他们去托儿所接孩子,招呼着他们的“泰勒”或“佐伊”时,3个小孩的同时回应仍会让他们大吃一惊。事实证明,他们本以为细致审慎的选择,到头来也是其他成千上万的父母们深思熟虑的选择。莱布尼兹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你看到两个时钟显示着同一个时间,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有3种解释:首先,它们的同步是连接它们的一条轴或线所致;其次,它们的同步是一个负责保证它们同步的熟练表匠不断调节的结果;最后,它们的同步归功于自身极其相似的运作机制。假如父母们不是通过彼此效仿来协调他们的选择的话,那么,其他那两种备案又是什么情况呢:一种受外因影响,另一种出于品位而独立开发出了相似性?
就外部因素而言,我们立刻就可以把那些常常被其他品位和时尚援引的各类影响排除掉。在与妻子一起给他们的女儿取名“瑞贝卡”之后,社会学家斯坦利·李柏森(Stanley Lieberson)惊奇地发现,有太多太多的同龄人也给他们的女儿取了同样的名字。在这件事情的启发下,他出版了一本书,取名为《品位的问题》(A Matter of Taste)。他很清楚,单凭呼吁像他一样可能用这个名字给自己孩子命名的父母们是不能解释清楚这个名字的发展态势的:
国家档案登记处从来没有赞助过任何有关“国家瑞贝卡协会”的广告宣传活动,当然,它也从未做过任何诋毁那些争相使用这个名字的人的事。“瑞贝卡”的兴起与其他名字的退落所呈现出的激烈的竞争态势与“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之间的竞争并不完全一样。无论沃尔玛还是内曼·马库斯都没有促销过这个时尚潮儿的名字,也没有哪个厂家肯因为你给女儿取名“瑞贝卡”而为你打折优惠。
当然,此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外部影响因素。关于婴儿命名发展趋势的一个最流行的民间说法就是,家长们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时,常常会受英雄人物、领袖、演员或演员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希拉里·克林顿曾说过,她的父母是以攀登珠峰第一人的名字给她取名的。但她出生于1947年,而当时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西兰养蜂人,他是在1953年才登上珠峰的,那一年希拉里·克林顿已经6岁了。
李柏森仔细研究了婴儿名字的兴衰隆替与公众眼中著名人物(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虚构的)的宦海沉浮之间的关联。他研究的几乎所有例子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名人横空出世之前,他被命名的那个名字就已经处于上升的态势了。而这个名人的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名字的流行态势,使它的流行度再创新高——李柏森称之为“曲线骑乘”(riding the curve)。不过,它并不是最初引爆这个名字的导火索。
以“玛丽莲”为例,这个名字在20世纪50年代相当受欢迎,很多人都会认为,这要归功于玛丽莲·梦露的名望。遗憾的是,梦露之前的几十年,这个名字的使用率就已经开始飙升了,而且在1946年,当珍妮·贝克(Jeane Baker)用它做自己的艺名时,这个名字就已经相当流行了。事实是,在梦露成名之后,这个名字的流行度已处于下降趋势。对此,人们猜测这还是梦露的功劳:在循规蹈矩的20世纪50年代或女权主义初期的60年代,人们不希望用一个性感女星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女儿。不幸的是,这种猜测又是个错误——20世纪30年代,这个名字就达到了流行的鼎盛期,而当梦露一夜成名时,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在李柏森调查的一些例子中,一个真实的或虚构的名人还真能带来一个新名字。20世纪60年代,英国引入了一部情景喜剧《家有仙妻》(Bewitched),剧中一个女巫的丈夫名叫达伦(Darren),在此之前,英国人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还有麦迪逊,这个当前已经名列最受欢迎女婴名字第三位的名字之前根本就没有被用来命名过任何女孩,直到1984年《美人鱼》(Splash)上映后,情况才发生了转变。电影《美人鱼》中,达丽尔·汉纳(Daryl Hannah)扮演的美人鱼爬出了东河,在路标上发现了“麦迪逊”(Madison)这个词,于是便用它做了自己的名字。此外,李柏森还发现了一些由著名的名字引发的突发性变迁。在20世纪30年代,“赫伯特”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富兰克林”则处于上升趋势;而自那以后,“阿道夫”便彻底消失了;众所周知,这3种情况都是事出有因的。不过,总的来说,名人名字的断续性主要是人们的认知错觉。人们在回想起一两个这样的例子,例如,名字由于名人而闻名、许多婴儿都用同一个名字命名时,于是他们便推测说,第二种情况是第一种情况的成因。当然,他们无法为了确保时间的正确性而按照年代来排序名字;也无法回忆起一些反例,例如,成千上万的婴儿本应该也被命名为汉弗莱、宾、卡里、赫蒂、葛丽塔、埃尔维斯等(但他们却没有被这样命名)。人们并不擅长区分因果关系。编剧们必须用更合理的名字为他们的角色命名,而志向远大的演员则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耐人寻味的艺名。很显然,他们承受着与当今准父母们为孩子取名时所承受的同样的压力。
那么,其他像民族主义、宗教、性别角色等这样更大的社会趋势对命名又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的结论仍然有悖于你的想象力。最近几十年见证了《圣经》中一些人名的复苏,比如,雅各、约书亚、瑞秋、莎拉等。对于这种现象,几乎每个人的第一个猜测都是,它反映了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复兴。不幸的是,李柏森的研究却表明,在此期间,《圣经》中人名的使用趋势与宗教活动的走势恰恰相反。而且,与未用《圣经》中的人名为子女命名的父母相比,那些选择了这些名字的父母并不比其他人更信奉宗教。相比之下,女权主义对命名的影响似乎会更大一些,遗憾的是,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基于花名的女孩名开始没落(如玫瑰、紫罗兰、菊花);但与此同时,其他同样基于花名的女孩名却变得越发受欢迎起来(如百合、茉莉)。在绘制那些由男孩名加小词缀派生出的女孩名的流行趋势时,你也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流行走向:一些呈下降趋势,例如,罗伯塔、宝拉、弗里达;而另一些则呈上升趋势,比如,埃里卡、米凯拉、布丽安娜,当然还有斯蒂芬妮。
造成这种世俗认知与事实之间差距的原因是,多数人的文化变革理念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变革是由可预测的外部因素所影响的结果,例如,政府、广告商、名人、经济、战争、汽车、技术等外部因素。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文化变革是易于理解的,换言之,他们认为,人们可以用解释个人行为方式的方法来解释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作家爱德华·特纳(Edward Tenner)曾经记录过一个与这种世俗认知谬误有关的实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公共场合,大多数男人都会戴一顶浅顶软呢帽,当然,今天几乎没有哪个男人会戴那种帽子了。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猜测从未间断过。有人说,是约翰·肯尼迪在其总统就职典礼之后首先开了不带礼帽的先河。有人说,人们搬到郊区居住后,他们要在汽车里花好多时间,因此,他们的脑袋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冷了,而且戴着个软呢帽也不方便从汽车里出出进进。还有人说,男人留长发已经成为一种个性标志,他们不想把头发藏起来,更糟的是,如果戴着帽子,他们还得忍受“帽头”的尴尬。此外还有一种强调自然的说法,认为帽子代表了自然的不完善性。还有人认为,帽子与政治体制有关,而年轻一代反对政体。也有人认为,文化开始转向对青年人的推崇,而帽子只与老年人有关。
在有关社会发展趋势的报道中,这种流行社会学的解释随处可见。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如果你对男性帽饰在过去几十年里的流行趋势做一下定量研究,你就会发现,自20世纪20年代起,它一直处于稳步下降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刚好见证了它的最后一搏,当时帽子的佩戴情况刚好降到了临界点以下)。这种下降趋势恰好与同期妇女佩戴帽子和手套的下降趋势平行。在上面那些流行社会学的解释中,没有一种说法与这些事实的编年史相符。可以说,那个时代确实有某种事情正在进行——那就是各个生活领域的繁文缛节正在日益减少,其中包括服装、仪表、公共举止以及称谓语(例如,用名字代替先生、女士,或者某某先生)。换言之,任何一种外因或目的(战争、政治、经济、科技)都无法稳步地将这种时尚趋势从20世纪20年代推向21世纪以及其后的年代。针对女性裙长的定量研究也得出与此相同的结论。与大众的观点恰恰相反,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裙长确实表现出了缓慢、平稳的跌宕起伏,但女性裙子的长短与股市、面料短缺、具有高度刺激性的广告活动或别的什么东西毫不相干。
李柏森认为,我们必须对到底应该如何解释文化变革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趋势”是指,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在对他人所做的决定进行预期与反应的同时,作出个人决定的集总效应(aggregate effects)的简称。这种效应催生了一种变革的内动力——一年中帽子佩戴的情形影响着下一年的情形。同时,它还促成了具有自身逻辑的其他各种趋势,而不是去随声附和作为整体的社会选择。
许多时尚——裙子长度、西装翻领的宽度、尾翼、胡须,当然还有婴儿的名字经历的都是此起彼伏的平滑波动,而不是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突起突降,或是股市般的变化无常。虽然调用一个诸如动力或钟摆运动的隐喻来解释一种趋势的变化并不是件难事,但我们还是需要对为什么可以用这类隐喻,而不是其他类型的隐喻这一问题作出解释。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艺术评论家昆汀·贝尔(Quentin Bell)指出,时尚周期可以用身份心理学来解释。精英们想通过服饰将自己与凡夫俗子区别开来,但随后,仅次于精英的人群也开始对他们的着装打扮进行效仿,接下来是再下一层民众的效仿,直到这种风格惠及黎民大众为止。而当另一种新的时尚出现时,精英们又转向了那种新时尚,于是,中产阶级又开始模仿他们,然后是下层中产阶级,以此类推,便形成了内部推动的无休无止的跌宕起伏的时尚大潮。(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道金斯利用加热器和冷却器对另一种身份象征的进化——即凤凰雀尾巴的类比。)按照传统,身份等级是用财富和阶级来计算的,不过,在不同的圈子和团体中,它也可以由其他声望指数来计算,比如,威望、时髦、精于世故。
李柏森补充说,一种时尚的前沿会尽可能一直朝着同一方向推进,因为任何回溯都将使潮人们企图与众不同的目的落空。这就是所谓的隐喻性动力(metaphorical momentum)。但它也有到达极限的时候——裙子再短也不能短过吊袜的束腰带,裙摆再长也不会超过6米。届时,精英们会被迫将这种风格反转过来的。这就是所谓的隐喻性钟摆(metaphorical pendulum)。听起来,它似乎什么都可以解释,但这恰恰说明,它实际上什么都解释不了。不过,李柏森也指出,每当一种时尚潮流复兴的时候,潮流先锋们总会同时将一些“其他”变革引入其中。因此,新潮的裙子、胡须、挡泥板永远不可能与上一个10年的潮流式样相混淆。
这又将我们带回到名字的问题。与西装翻领大小的流行趋势不同,人名并不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的音节首辅音(onsets)或音节尾(codas)的声音、它们的词源(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凯尔特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它们的字面意思(鲜花、珠宝、武器、月份)、它们与名人的联系,等等。名字有着庞大的词库资源,它可以由小说来填补(“米兰达”来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温迪”来自《彼得潘》);由姓过渡到中间名,进而再过渡到第一个名字(比如,摩根和麦肯齐);外来名(例如,索伯汉、纳塔莉亚、迭戈);通过加前后缀,例如,-a、-ene、-elle,非裔美国人则加La-、Sha-、-eesha(例如,Latonya、Latoya、Lakeesha,等等)。难怪不同阶级和种族群体会从不同的名库中选择自己的“样本”。
一方面,大多数父母想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以避免和周围小朋友同名,山姆·高德温(Sam Goldwyn)曾建议一个员工“千万别给你儿子取名威廉。几乎每个姓汤姆、迪克和哈利的名字都叫威廉”;另一方面,父母们又不想让自己孩子的名字过于另类,免得让人觉得这个孩子来自一个不谙世故或者离群索居的家庭。在这个时尚的一个极端上,我们有女演员瑞秋·格里菲斯(Rachel Griffiths),她给儿子取名Banjo(班卓琴);魔术师佩恩·吉列特(Penn Jillette),为其女儿取名Moxie Crime-Fighter(魔蝎座·通天干警);摇滚歌星鲍勃·吉尔道夫(Bob Geldof),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叫Little Pixie(小精灵)、Fifi Trixibelle(菲菲·特丽克丝贝利)和Peaches Honeyblossom(蜜桃·蜜花)。而在另一个极端上,美国有位拳击手乔治·福尔曼(George Foreman),他的5个儿子都叫乔治。例外总归例外,在选择名字时,大多数父母都喜欢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问题是,由于每个家长都不想走极端,又都想与众不同,结果就是,他们对孩子的命名如出一辙。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中小学里到处都是叫苏姗和史蒂夫的孩子,现在又到处都是克罗伊和迪伦。不过,请不必担心,未来的父母们将会对这种史蒂夫或者迪伦过热现象作出积极的回应,他们会找到一个全新的名字,从而将这一潮势扭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这种动态不禁让我想起了尤吉·贝拉(Yogi Berra)的那句酒店评语:“没有人再去那儿了,那儿的人太多了。”婴儿取名顾问们,比如帕梅拉·撒特兰(Pamela Satran)试图向家长们建议一些既不俗又不怪异的名字——也许是一些英雄的名字,例如,莫奈、柯法斯;或者某种颜色词,比如,灰褐色或者蔚蓝色。(Yogi[瑜珈信徒],听过有人叫这名字吗?)
象声词是挖掘中庸名字的强大劲旅。一个流行的名字将它的魅力传播给那些与其共享同一个音节首辅音、音节或音节尾辅音的现成名称。20世纪早期,珍这个名字引出了贾尼斯、珍妮特、简、詹妮尔,这几种名字各自都有许多种不同的拼法。卡罗尔引出了卡洛琳、凯伦、凯莉、卡拉、卡丽娜。最近,詹妮弗这个名字中的“詹”字催生了杰西卡和詹娜,“妮弗”则催生了希瑟和安布尔。李柏森指出,许多被归因于名人效应的流行名字(珍妮特·盖纳、杰西卡·兰格)确实只是对流行语音的追捧。因此,象声词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一些名人的名字会渐渐石沉大海。举例来说,20世纪60年代,达伦在英格兰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而其他电视角色的名字却没这么幸运(例如,瑞奇和麦克斯韦),因为在当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英国男孩名字都是以n音结尾的。
在几乎所有文化中,男孩与女孩的名字均有所不同,很显然,这是性别在起作用。然而,性别在命名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止这些。父母们偶尔会给他们的女儿取一个男孩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能有个男孩。不过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那就是,他们希望藉此暗示女孩子们要自立自强。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名字往往会落在那些命中注定成为性感女星和模特的女孩子头上(或者是她们自己选择了这类名字),比如,德鲁·巴里摩尔、布莱尔·布朗、格伦·克洛斯、杰米·李·柯蒂斯、卡梅隆·迪亚兹、杰瑞·霍尔、达丽儿·汉娜、梅尔·哈里斯、詹姆斯·金、肖恩·杨(所有这些人的名字都是与她们同龄的女孩子所不常使用的)。要不是女权运动的进程已经持续了百年或者更长时间,它应该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在20世纪初,贝弗利、黛娜、伊芙琳、盖尔、莱斯利、梅瑞狄斯、罗宾、雪莉等名字主要用于男子。在这一时期里,男女同名命名只是单方面的。一个男孩的名字一旦过多地被用于女孩,这个名字就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这大概是因为父母们能够接受将男孩的特征赋予女孩,但却无法接受将女孩的特征赋予男孩。正如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所说:“生活对于一个叫苏的男孩子来说是件不易的事情。”
年龄是流行趋势的另一个推动力。许多名字和声音随着它们主人的年迈而变得缄默,以至于最终被遗弃,因为家长们不想将他们的孩子想象成小老头或小老太太。这就是许多这类名字的劫数吧,比如,埃塞尔、多萝西、米尔德里德以及以-s(斯或丝)结尾的名字,例如,格拉迪斯、弗洛伦斯、路易斯、多丽丝、弗朗西斯、艾格尼丝。一旦它们的主人过世或失踪,这些名字便会失去它所固有的那种年迈的含义,并重新被人们召回,其条件是,它们必须符合新时代象声词的最强音。举例来说,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约瑟夫就曾获得过重生,假如你发现自己属于马克斯、玫瑰、山姆、苏菲、杰克、赛迪中的一员,那么,你不是在养老院长大的,就是在托儿所长大的。
我们所说的这些与一个新词能否被接受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我曾说过的,在某些方面,名字与其他词类是不同的。当名字被用于命名孩子时,每个人都会得到命名,但名字的资源库是有限的,而且,一般来说,名字都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当它被用于命名概念时,许多概念却依然是难以名状的,那些被命名的概念往往会得到一个新的声音组合,而大多数年度词语的存活时间都短暂得可怜。尽管如此,驱动人名时尚循环的内动力仍然部分地适用于造词和其他词类的接纳。
前面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公司及其商品的名称时尚,从别克到野马再到伊兰特。此外,与名称时尚一样,青少年、校园、潮人俚语等时尚趋势,例如,the cat's pajamas(卓越的人或物)、hep(玫瑰)、groovy(时髦的)、far out(激进的)、way cool(很酷)、phat(酷毙了)、da bomb(太牛了)也可以被准确地测定出来。还有另外一种时尚周期,它特别青睐那些表示最高级的术语。说话者总是想用自己的非凡经历去打动他们的听众,于是,他们就采用了形容词的最高级来描述它,遗憾的是,这种做法贬低了最高级的原始价值。因此,紧随其后的说话者就只能求助于某个表示极度经验的词,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最高级,依此类推,一个螺旋式的语义膨胀就这样产生了。很久以前,语言前辈们曾经对一些词的原始含义进行了淡化处理,例如,terrific(引起恐慌)、fantastic(值得幻想)、tremendous(使人发抖)、wonderful(鼓舞人心的奇迹)、fabulous(虚构的显赫)。最近几十年间,人们又对下面一些词的原始含义做了同样处理,例如,awesome(了不起的)、excellent(优秀的)、outstanding(出色的),在英国还有brilliant(杰出的)这个词。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人类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领域,它们高度地受控于情感,比如,性、排泄、老年化以及疾病等,用于这些概念的术语往往运行在我所说的“委婉跑步机上”(euphemism treadmill)。由于与某个令人堪忧的概念间的联系,它们会被玷污,于是人们便用另一些未被污染的术语来取代它们,然而,这些术语也同样逃脱不了被污染和取代的噩运。举例来说,toilet原本是个表示身体护理的术语(例如,toilet kit[如厕工具包]和eau de toilette[盥用水]),后来被用来指称排泄设备和场所。随后,它又被bathroom(浴室、厕所)取而代之,于是就出现了下面这些荒唐的说法,例如,The dog went to the bathroom on the rug(狗在地毯上如厕)、In Elbonia, people go to the bathroom on the street(在艾尔波尼亚[9],人们在大街上如厕)。当bathroom再次遭到玷污后(例如,在一些厕所幽默中),它又被滔滔而至的其他术语所取代,例如,lavatory(盥洗室)、WC(洗手间)、gents’(男洗手间)、restroom(更衣室)、powder room(化妆室)、comfort station(公共厕所)等。与此类跑步机式循环术语类似的还有其他类术语,例如,指称残疾人的lame(跛足的)、crippled(致残的)、handicapped(有缺陷的)、disabled(不能自理的)、challenged(受到挑战的);指称令人不悦的职业的garbage collection(垃圾回收)、sanitation(环境卫生)、environmental services(环保服务);指称学术活动的gym(健身)、physical education(体育)、human biodynamics(人类生物动力学);指称受压迫少数民族的colored(有色人种的)、Negro(黑人的)、Afro-American(美国黑人的)、black(黑人的)、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国人),等等。
在时尚大潮面前,即使是科学也只能随波逐流。人们原本以为科学家们会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他们的发现命名,比如ligand(配合基)、apoptosis(细胞凋亡)、heteorskedasticity(异方差性),结果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术语首先让位给了英语中的那些遁词(circumlocutions),例如,frequency-dependent selection(依赖频率的选择)、secondary messenger(第二信使),进而又让位给了更加异想天开的引喻,比如,quark(夸克)、Big Bang(宇宙大爆炸)以及Sonic Hedgehog(音猬因子)——一种以视频游戏角色的名字命名的基因,而现在,它已经让位给了截词(hip truncations),例如,物理学中的brane theory(膜理论),其中的brane截自英语单词membrane(薄膜)。
请注意,时尚的潮涨潮落并不是决定一个词语存亡命运的唯一内动力。即使一个新词的品位保持稳定,其成功与否仍然取决于词语流行病理学(lexical epidemiology)——一个新词从始创者到一个新的采用者的传播方式。当然,这个人还将继续将其传播给下一个使用者,一传十、十传百,辗转无穷。最终,这个新词要么渐渐消失,要么被地方的流行方言所接受,这取决于了解它的那个人一天之内对多少人谈及过它,还取决于听说过它的那些人对它的关注及乐于记忆的程度。就像真的流行病那样,人们很难预料究竟结果会如何。换言之,一个新词在上口度、熟悉度、可信度,或者第一个采用者的魅力等方面的细微差别,决定着它最终能否打进一个语言社团并被人们世世代代相传下去的命运。在这个背景下,梅特卡夫提出的那5个成功秘诀(即FUDGE)中的频率性和多样性才有了真正的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词语和人名传播途径的考察颠覆了传统的文化起源与发展观。20世纪,人们将文化看成是一种追求目标、发现意义以及刺激反应的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它既可以是人类进行操纵的牺牲品,也可以是人类参与干预的受益者。然而,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实践活动,名字的兴衰命运并不符合这种文化模式。尽管名字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它们却并不反映其他社会趋势,也不受其他榜样的推动。它们所受到的唯一一次影响来自于那条“麦迪逊大街”,其结果是,发生在那条大街上的一系列离奇的美人鱼事件使得麦迪逊这个街名成为全美第三流行的女孩名。要想搞清楚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对人性在命名决定中所表现出的特征进行仔细观察——地位心理学、家长心理学以及语言心理学,再加上之前的命名者们的选择结果以及前面提到过的观念流行病心理学(epidemiology of ideas)——一个几乎还不存在的学术领域。
在1978年出版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一书中,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呼吁人们关注一些突发的、非必要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往往出现在人们进行个人选择时,因为这些个人选择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选择。谢林提到的一个例子是城市被隔离的方式。一个城市被隔离开来,并不是政府的隔离政策所致,也不是人们只希望和自己的同族住在一起,而是没有人愿意成为自己居住区中的少数外族人之一。出于避免被边缘化的目的,当一个个家庭不断地搬进搬出的时候,它们就成了这个社团的一部分,并影响着其他家庭何去何从的选择。最终,黑人与白人两个截然不同的社团出现了,也就是说,无论哪种社团都不是谁设计出来的,或者是谁需要的。谢林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有关车道被堵:当现场的每一个司机都放慢几秒车速并伸出脖子去观望一场交通事故时,车道就有可能被堵住——这是一场假如司机们之前没有放慢车速看热闹的话,没有人会接受的、为了摆脱拥堵所进行的讨价还价。谢林还解释了在人们的个人决定相互影响时,这些模式就产生了的原因:
如果你的问题是交通太拥堵了,那么你本人就是交通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你因为喜欢人群而加入一个人群,那么你就为这个人群增加了一员。如果你因为那些和你的孩子一起上学的小学生而将自己的孩子从学校带走,那么你就带走了一个和“他们”一起上学的小学生。如果你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提高嗓门,那么你就增加了其他人为了让他们的声音能被别人听到而发出的更高的噪声。当你剪短你的头发,你所改变的只是其他人对人们留了多长头发的印象。
最近,在一本名为《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的畅销书中,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lm Gladwell)将谢林的观点应用到一些社会趋势的解释中,例如,识字率、犯罪率、自杀率、青少年吸烟率的变化。传统观点将以上每种趋势都归因为外部社会力量,例如,广告、政府计划或各种榜样模式。事实上,它们的真正驱动力并不是这些外因,而是个人选择、影响及其反馈等内部动力在起作用。婴儿的命名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事物命名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佐证,在这个佐证中,一种大规模社会现象——语言组合,出人意料地从众多彼此影响的个体选择中浮出了水面。
乍看起来,一个名称似乎很简单——它不过是一个语言社团共享的声音和含义的结合体而已。然而,当我们走近它的工作原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人类经验领域。在之前写的那些书中,我曾对名称是如何在一个人的大脑中表征的问题进行过反复探讨。我也曾为一个人到底能够了解多少词语、儿童习得词语到底有多迅速、词语的构造到底有多优雅、大脑对它们的识别到底有多难等问题而惊叹不已。在本章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概念结构在捕捉词义时表现出的精确性和抽象性。在这一节中,我们又看到了名字是如何将我们与我们头脑之外的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名字从命名者那里获得含义,该命名者首先选定一个声音,用它来指称一个个体或一类事物,然后再将他选择的这个声音传递给一系列意欲用同样方式使用这个声音符号的人们。而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会将我们卷入到一起具有讽刺性意味的事件当中去。指称行为以及复制它的意图将我们与现实直接连接在一起,而绝不仅仅是将我们与我们对现实的设想连接在一起,尽管人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很难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以将一种巨大的矛盾压缩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一种声音的选择将我们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矛盾正处于人类随波逐流与匠心独具的两种不同欲望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