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语言的其他形式那样,诅咒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它的普遍存在是有条件的。当然,由于时空的变迁,被视为禁忌语的那些具体词语和概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语言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些原本干干净净的词语变得越来越污浊不堪,相反,一些原本肮脏下流的词语却被岁月漂洗得一尘不染。举例来说,当今天的英语使用者在早期的医学教科书上读到“女性膀胱颈短,靠近the cunt”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为此大跌眼镜的。然而,这是《牛津英语字典》援引自15世纪课本中的原话。记录此类语言演变的历史学家杰弗里·休斯(Geoffrey Hughes)指出:“随着生机勃勃的男性内裤广告的问世,蒲公英可以被称作pissabed、shitecrow、windfucker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禁忌语命运的变迁还直接影响着一部文学作品的可接受性。举例来说,因为“黑鬼”(nigger)一词,《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不止一次被美国学校定性为禁书。尽管这个词从来就不是个礼貌术语,但是,对于当今的读者来说,它远比在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的煽动力更强。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词语也从它们的禁忌身份中解放了出来。《卖花女》(Pygmalion)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一次上流社会的茶会上,女主角伊莉莎·杜利特尔尖声地喊道:Not bloody likely!(这绝对不可能!)1914年,这部作品被搬上了银幕,电影中,杜利特尔的这句话不仅令她身边的那些虚构人物心生反感,就连观众也无不对她嗤之以鼻。然而,到了1956年,当这部作品被改编成音乐剧《窈窕淑女》(My Fair Lady)时,bloody(血腥)一词已经变得毫无惊艳之处,以致编剧们竟然担心这个词是不是还能达到原来的诙谐效果。为此,他们还特意添加了这样一个场景——伊莉莎被带到爱斯科特赛马会上,她朝一匹马尖声地喊道:Move your bloomin’arse!(甩开你的大屁股,快跑啊!)现在,许多父母都经历过这样的难堪,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天真无邪地使用着一些动词,如,suck(吸吮)、bite(咬)、blow(吹),殊不知,这些词均源于描写口交(fellatio)的词语。不过,家长们是否也考虑过他们自己也不加思索地使用着那些如今被视为无伤大雅的单词呢?比如,sucker(笨蛋,源自cocksucker)、jerk(混蛋,源自jerk off)以及scumbag(人渣,源自condom)。在这方面,喜剧演员们曾做过很多努力,他们希望通过不断地重复使用这些猥亵词语,使之最终达到脱敏点(the point of desensitization,也就是心理语言学家所说的语义饱和过程),或者瞬间将自己扮演成语言学教授,以此呼吁大家去关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原则。以下片段摘自著名的莱尼·布鲁斯语录。
Tooooooo是个前置词。To是个前置词。Commmmmme是个动词。To是前置词。Come是个动词。To是个前置词。Come是个动词,一个不及物动词。To come.To come……这就像一个大架子鼓的独奏:To come to come, come too come too, to come to come uh uh uh uh uh um um um um um uh uh uh uh—TO COME!TO COME!TO COME!TO COME!—Did you come?Did you come?
Good.Did you come good?Did you come good?Did you come?Good.To.Come.To.Come—Did you come good?Didyoucomegooddidyoucomegood?
下面这个片段摘自卡林关于“7个禁忌语”的独白。
Shit、Piss、Fuck、Cunt、Cocksucker、Motherfucker还有Tits,哇。你知道,Tits根本不应属于这个列表。它听起来如此亲切,像个昵称。听起来像一个昵称。“嘿,Tits到这儿来。Tits,这位是Toots。Toots,这位是Tits。Tits,这是Toots。”它听起来像一份小吃,不是吗?是的,我知道,它确实像。不过,我并不是暗指那个男性至上主义的小吃,我是想说,新纳贝斯克(食品公司)Tits、新奶酪Tits、玉米Tits以及比萨Tits、芝麻Tits、洋葱Tits、马铃薯Tits,是的。
现在,tits这个词已经是个干净的词语了,它已不会被列入《清洁电视广播法案》,而且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严肃报刊“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即《纽约时报》上。[12]不过,并不是所有禁忌语都有tits的运气,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中的许多词语始终被禁忌着,而且,就像Steve(史蒂夫)的兴衰史那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哪些词会被净化、哪些会被污染,一直是个变化莫测、反复无常的迷。
类似的脱敏运动(desensitization campaigns)将目标指向了一些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浑名,在这类人群内部,人们尽量有意地、堂而皇之地使用这些浑名,目的是希望将它们“沙化”(reclaim)。因此,我们的语言中有NWA(Niggaz With Attitude,即暴躁的黑鬼,一个黑人嘻哈乐团)、Queer Nation(酷儿国度)、queer studies(酷儿研究)、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美国一档极其火爆的电视节目《粉雄救兵》,一群在各行各业有成就的男同性恋者为在事业和生活各个方面失意的异性恋男人出谋划策的故事)、Dykes on Bikes(机车女同志,一群骑摩托车的女同性恋)及其网址www.classicdykes.com;我们还有Phunky Bitches(在线婊子),一个“面向女性(以及男性)的实时在线社团,致力于现场音乐表演、旅游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在(犹太)寺庙兄弟会上,我从来没有听过会员们互相这样打招呼:“咋样,犹太佬!”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小说家金基·弗里德曼(Kinky Friedman)却领导了一个取名为“德州犹太小子”的乡村乐队,此外,还有一本专门为年轻犹太读者创办的嘻哈杂志,取名为Heeb(对犹太人的蔑称)。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词语并没有被中性化成反抗和团结的象征,准确地说,这是因为在大多数语言社团里,它们仍然具有很强的冒犯性。倒霉总是青睐那些不知情的局外人,在电影《尖峰时刻》(Rush Hour)中,成龙扮演了一个香港侦探,他傻傻地模仿着他的非裔美国人搭档向一个洛杉矶酒吧黑人老顾客打招呼“咋样,黑鬼”,于是引起了一场小骚乱。
当一种语言中的某些特定词语进入另一种语言时,它们的攻击力会变得更加强大。在魁北克法语中,merde(相当于英语中的shit)远比其英语对等词shit温和,它更接近于英语中的crap的意思;此外,还有con(相当于英语的idiot)这个词,大多数人至多也就依稀地知道,它原本是cunt的意思。这还不算最糟糕的,在魁北克法语里,最糟糕的是你对一个人说Tabernac!(相当于英语中的tabernacle[圣体龛])、alisse!(英语chalice中的[圣杯])、Sacrement!(英语sacrament中的[圣餐])。2006年,天主教会将这几个词语连同它们的原始宗教定义喷绘在户外广告板上,希望借此沙化这些词。(一位专栏作家感叹道:“难道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吗?”)目前,在其他天主教地区,宗教亵渎语十分常见,这种情况与英格兰宗教改革前的情况十分相似,有关性和粪便的各种术语泛滥成灾。
不过,除了这些跨时空的语言变体外,我敢说,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中(或许是全部)都存在着许多用于非高雅社交场合的、富有情感的词语。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也许当属澳大利亚的Djirbal语,一种当地的土著语言。这种语言的特点是,只要是在婆婆和某些堂兄妹面前,“每一个词”都是禁忌语。当这些亲属在身边的时候,人们不得不使用一套完全不同的词语(尽管语法相同)。当然,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像英语和法语那样,其他大多数语言中的诅咒词语一般都来自这些有限的话题:性、排泄物、宗教、死亡与疾病,此外还有一些令人不爽的社会群体。
对于声称某某语言中根本没有猥亵语的言论,我们不得不采取客观的接受态度。事实是,在许多地区,假如你要求那里的人列出他们的脏话,他们很可能会表示抗议。但请不要忘记,脏话和虚伪总是结伴而行的,一些性格调查问卷甚至将人们对“我有时说脏话”作为核实一个人是否说谎的选项。在《污言秽语已删除:对脏话的认真思考》(Expletive Deleted:A Good Look at Bad Language)一书中,语言学家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
利用我获取日语数据的问题,我的一个被调查者,一位娶了日本女人的英国绅士,对他的妻子进行了问卷调查。她告诉他,她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日语中有什么脏话。在明知自己丈夫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她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望着自己的丈夫所说的这番话确实让人领教了她在这方面的本事。
《亵渎性格言:言语侵犯研究国际期刊》(Maledict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erbal Aggression)上的一篇综述文章中收录了大量的性侮辱和低俗的日语词语,此外,发表在那本期刊上的其他跨文化调查也给出了一些类似的词汇表。
事实上,禁忌语只是一种叫作“咒语”(word magic)的语言现象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咒语所涉猎的范围更大。尽管音、义结合的任意性是语言学的基础前提之一,但多数人却直觉地认为,这其中一定还潜藏着其他奥秘。他们将一个实体的名称作为其本质,因此,说出一个名称这样简单的行为却被看成是对其所指称物的侵犯。
咒语、法术、祈祷以及诅咒是人们试图通过言语影响世界的一种途径,相反,禁忌语和委婉语则是人们尽量不去影响它的一种手段。在提及一个期盼的事件之后,就连那些头脑冷静的唯物主义者们也会下意识地敲敲木头[13];而当提及一桩可怕的事情时,他们则会插上一句God forbid(上帝禁止它,即但愿别发生这种事);也许出于同样的原因,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在他的办公室门上挂了一只马蹄铁:“我听说,即使你不信它,它也会显灵的。”
禁忌语最擅长捕获人们的注意力
咒骂的普及性及其威力表明,禁忌词语很可能被接进了情绪脑(emotional brain)的古老而深远的部位。在引言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词语不仅有外延而且还有内涵:一种与该词字面所指并不完全等同的情感色彩,例如“有原则的”之于“顽固的”、“窈窕的”之于“骨瘦如柴的”。这种语义上的差别让我们想起了禁忌词语与它们的近义词之间的区别,例如,shit与feces、cunt与vagina、fucking与making love等。早在很久以前,心理语言学家们就甄别出了词语内涵的3个主要不同方面:好与坏、弱与强、积极与消极,尽管内涵肯定还会有其他维度。举例来说,“英雄”是好的、强大的、积极的;“懦夫”是不好的、懦弱的、消极的;“叛徒”是邪恶的、软弱的、主动的。所有禁忌词都汇集在非常坏、非常强的边缘地带。
那么,内涵与外延真的被存储在大脑的不同部位了吗?其实这并没有什么难以置信的。除了其他系统外,哺乳动物的大脑中还有一个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该系统是一个调节动机和情绪的古老的网络系统、一个新大脑皮质(neocortex),即大脑的褶皱表面,它随着人类的进化而激增,它是感知、知识、推理和规划的加工中心。这两个系统相互关联、协同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词语的外延集中在新大脑皮质,尤其是在大脑左半球,而词语的内涵则遍布新大脑皮质与边缘系统的连接处,尤其是在大脑的右半球。
在边缘系统内部可能存在着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大脑杏仁核(amygdala),一个埋在大脑颞叶(两侧半球每侧各一个)前部的、杏仁状的器官,它协助大脑授予人们记忆与情感。一侧杏仁核被移除的猴子虽然还能学会识别一种新形状,比如一个带条纹的三角形,但却很难再学会那些预示令人不快的事件的形状(比如一次电击)。就人类而言,当一个人看到一张愤怒的面孔或者一个令人不快的单词,尤其是一个禁忌词时,其大脑中的这个杏仁核就会被“点燃”——在大脑扫描中,它会表现出更多的代谢活动。事实上,在还未掌握扫描工作中的人类大脑这项技术之前的很多年,心理学家们就已经掌握了测量一个禁忌词影响人的情绪的技术,他们将一个电极绑在人的手指上,测量由突如其来的汗波(wave of sweat)所造成的皮肤电传导的变化。这种皮肤反应伴随着杏仁核内部的活动,而且,正如从杏仁核本身记录下来的内部活动那样,它可以由禁忌词触发产生。词语的情感色彩或许是在儿童时期习得的:在表达思想方面,双语使用者们通常会觉得自己的第二语言在表达思想上不如第一语言那么酣畅淋漓,相比于第二语言,第一语言中的禁忌词语和谴责更容易令他们的皮肤作出相应的反应。
双语使用者这种下意识的不寒而栗是由听到或读到一个来自语言系统某个基本特征的禁忌词触发的:词义的理解是机械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可以将不想听的声音拒之耳外的“耳塞子”(earlids),而是因为,一旦一个单词被看到或听到,我们根本无法将它当作一幅涂鸦或一声噪声;相反,我们会条件反射般地在记忆中进行搜索,并对其含义作出相应的反应,其中包括它的内涵。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斯特鲁普效应(Stroop effect)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打开任何一本心理学教科书,你都可以看到有关这个实验的介绍,不仅如此,到目前为止,仅围绕这一主题撰写的科学论文就有4000多篇。这个实验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实验人员要求受试者迅速观看一个字符串列表,然后让他大声地说出每个字符的印刷颜色。下面请你试一下这组字符,从左向右依次大声说出:black(黑色)、white(白色)、gray(灰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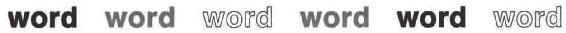
这应该是个极其简单的任务。再请看下面这组字符,这一组字符应该更容易说出。

现在请注意,说出下面这组字符将要比说出上面那两组困难得多。

针对上述现象,心理学给出了如下的解释:就识字的成年人而言,朗读单词这种技能已经被他们过度习得(overlearned)至一种强制的程度:即使你设法忽略这些词语的含义,而将精力集中在它们的印刷颜色上,你也无法用主观意志力将这一过程“关闭”。这就是为什么当实验人员将字符安排成与其含义相同的颜色时,你就能迅速地读出它们,而当他们将字符安排成不同于其含义的颜色时,你的阅读速度就会减缓的原因。与此类似的表现还有口头命名的情况,实验中,实验人员要求人们对下面这样的颜色块进行命名。

当受试者佩戴的耳机里传出“黑色、白色、灰色、白色、灰色、黑色”的指令时,这组让人分神的颜色词顺序会加强这项任务的难度。
我们说过,禁忌语是最擅长捕获人们的注意力的。现在,你可以通过这个斯特鲁普效应来亲自感受一下它们在这方面的特长。下面请你尝试着命名这些单词的印刷颜色。

心理学家唐·麦凯(Don MacKay)也曾做了这个实验,他发现当人们的目光落在每个单词上时,一种下意识的犹豫的确减缓了他们的命名速度。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一个语者或作者完全可以利用一个禁忌词来唤起受众的情感反应,不过,这种做法相当违反他们的意愿。
一些企业利用仅次于禁忌语的名词为它们的产品命名,希望借此来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实际上,它们是在开发利用斯特鲁普效应的潜能,比如,那个名为Fuddruckers(福德洛克)的连锁酒店、FCUK(French Connection UK,意为英国法式连结)服装品牌以及电影《拜见岳父大人》(Meet the Fokkers)。在语言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对禁忌语的下意识反应实际上有助于塑造一种语言。我这么说的根据来自于一个语言版本的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坏的言辞将好的言辞驱逐出语言流通域。人们通常会避免使用那些可能会被误解为脏话的术语。Coney原本是一个指称rabbit(兔子)的旧名称,它与honey(蜂蜜)谐音,但在19世纪晚期,它退出了语言历史的舞台,究其原因,这很可能是因为它听起来有点过于接近cunt了。与coney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下面这些词的礼貌含义:cock、prick、pussy、booty以及ass(至少美国人用ass;英国人仍然用arse这个粗鲁名词,ass在英国只有驴子的意思)。取名Koch(科赫)、Fuchs(福克斯)、Lipschitz(李普希茨)的人,常常会改变他们的姓氏,比如,Louisa May Alcott(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家族)之前的姓氏是Alcox(阿尔科克斯)。1999年,在一次管理层会议上,由于在预算中使用了niggardly(吝啬的)这个词,华盛顿特区市长助理被迫辞职。原因是,他的一个同事对这个词非常不满,事实上,niggard(吝啬鬼)是一个中古英语词,意为miser(吝啬鬼),而nigger(黑鬼)这个绰号则是从几个世纪之后才进入到英语中的西班牙语negro演变而来的,在西班牙语中,negro是个表示“黑色”的单词。换句话说,niggardly与nigger毫不相干。然而,无论对市长助理或niggardly这个单词来说有多么不公平,niggardly这个词注定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厄运。同样的厄运还降临到了queer(奇怪的/同性恋)和gay(快乐的/同性恋)这两个指称同性恋者的名词的原始含义上。
正如听到别人说脏话那样,大声咒骂将触及大脑深处那个古老的部位。失语症(Aphasia)是一种语言遗失现象,由脑皮质和脑白质损伤造成,脑白质沿着大脑横断面(大脑外侧裂)潜存于大脑的左半球中。神经学家们几乎在失语症研究初期就注意到,失语症病人并没有丧失诅咒的能力。英国一个失语症病例的研究记录显示,该患者反复地说Bloody hell、Fuck off、Fucking fucking hell cor blimey以及Oh you bugger等。此外,神经病学家诺曼·格什温德(Norman Geschwind)还曾经对一个美国病人进行过跟踪研究,该患者因脑癌切除了整个大脑左半球。病人不能说出图片的名称、不能说或听懂别人的话语、不能重复多音节的单词,然而,在1次5分钟的采访过程中,他竟然重复地说了7次Goddammit、1次God和1次Shit。
失语症患者咒骂能力的幸存表明,禁忌的浑名是以预先构造的公式形式(prefabricated formulas)存储于大脑右半球中的。此类公式位于一端始于命题话语的连续统的另一端,在这个连续统中,按照语法规则,词语组合表达概念组合的含义。这并不是说大脑右半球里包含着一个脏话模块(profanity module),而是说明大脑右半球的语言能力受限于存储于记忆中的那些公式,而不是由规则制约的句法组合。一个单词就是一个典型的记忆组块(chunk),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的大脑右半球中都有一个相当数量的词汇表被用于话语理解。不仅如此,大脑右半球中可能还存储着一些由规则制约的语言特殊形式的对应体,如动词的不规则变化形式。此外,它还常常参与调配较长的记忆公式,比如,歌词、祈祷以及um(嗯)、boy(嘿,乖乖)、well yes(嗯,可以啊)等插入语,此外还有会话起始语,例如,I think(我认为)、You can't(你不能),等等。
我们说大脑右半球与脏话有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相比于大脑左半球,右半球更热衷于参与人们的情绪波动,尤其是消极情绪的波动。事实上,那些禁忌诨名也许并不是大脑右半球中的大脑皮层触发,它们很可能是由一个更早进化的大脑结构,即那个被叫作基底神经节的大脑结构所触发。基底神经节(basal ganglia)是一组深埋在大脑前半部的神经元集群。它们的环路会从大脑的许多其他部位接收输入,其中包括杏仁核以及边缘系统的其他部位,然后将这些信息回送到大脑皮质,主要是大脑前额叶(frontal lobes)。大脑前额叶的功能之一就是将运动或推理顺序打包进一些组块,当我们学习一种技能时,那些组块可以用来进一步重组。大脑前额叶的另一个功能是抑制那些被打包进组块中的行为的执行。由于基底神经节组件彼此相互抑制,因此,不同部分的损伤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果一部分基底神经节发生了退变,则很可能会引发帕金森氏病,其临床表现为颤抖、僵硬、运动困难。如果是另一部分基底神经节发生退变,则会导致亨廷顿氏舞蹈症,其临床表现为舞蹈性运动和失控性运动。
我们有两条证据线索可以证明基底神经节(扮演着行为的打包者和抑制者的双重角色)与人类的咒骂行为有关。一条线索来自于一个右基底神经节中风病人的病例研究,此次中风给患者留下了一种经典失语症的镜像综合征。该患者能用语法句进行流利的交谈,但却无法唱出自己熟悉的歌曲,无法背诵原本谙熟的祈祷文、祝福语或者脏话——即使你说出某句脏话的一部分并引导他将那句脏话补充完整,他也做不到。
除了打包者和抑制者的双重角色外,基底神经节在人类的咒骂行为中还扮演着一个更著名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图雷特综合征(Gilles de la Tourette Syndrome),或称妥瑞综合征(Tourette syndrome)或简称为妥瑞症(Tourette's)突然出现在很多电视剧的情节中,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这种症状十分令人费解。妥瑞症其实就是一种由基底神经节部分遗传性畸形造成的神经疾病。就像电视迷们所了解的那样,它最显著的症状就是发声痉挛,同时患者还会高声喊出猥亵的言辞、民族禁忌语及其他各类污言秽语。医学上称这种症状为秽语症(coprolalia),coprolalia这个希腊词根还见于下面一些单词,例如,coprophilous(癖粪的,生存于粪便之中)、coprophagy(食粪症,以粪便为食)以及coprolite(粪化石,石化的恐龙粪便)等英语单词。事实上,只有少数患有图雷特综合征的人才会患上秽语症,较常见的痉挛包括眨眼,面部肌肉迅速抽动,发出怪异的声音、重复的词语或音节。
秽语症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禁忌范畴,而且还包括了不同语言的相似含义,这一事实表明,诅咒行为确实是一种连贯的神经生物学现象。最近,一篇文献综述列出了下列一些美国图雷特综合征病人喊出的污言秽语,依次从最频繁到最罕见:
fuck、shit、cunt、motherfucker、prick、dick、cocksucker、nigger、cockey、bitch、bastard、tits、whore、doody、penis、queer、pussy、coitus、cock、ass、bowel movement、fangu、homosexual、screw、fag、faggot、schmuck、blow me、wop
病人也有可能喊出较长的表达式,例如,Goddammit、You fucking idiot、Shit on you以及Fuck your fucking fucking cunt。该文献还例举了西班牙语病人的秽语,它们是:puta、mierda、co?o、joder、maricon、cojones、hijo de puta、hostia。日语病人的秽语列表包括:sukehe、chin chin、bakatara、dobusu、kusobaba、chikusho以及一个在列表中被小心地界定为“女性的性部位”的空白。综述中甚至还报告了一个耳聋妥瑞氏症患者用美国手语表达的fuck和shit。
图雷特综合征患者突然爆发出的污言秽语不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经验,而是对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的反应,这就好比无法抗拒的瘙痒,或者愈演愈烈的眨眼或打哈欠的欲望一样强烈。这种无法拒绝的冲动与人类自我控制的较量让人想起了一种被称为“恐怖诱惑”的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简称OCD)——一种可能令人作出可怕事情的具有强迫性的恐惧,比如,在一个拥挤的剧院中高喊“着火了”或者把某人推下地铁站台。像妥瑞症(强迫症常常伴随妥瑞症)那样,强迫症似乎也涉及制动机制与基底神经节加速环路间的一种不平衡。这说明,基底神经节的作用之一是将某些想法和欲望指派成不可思议的东西——禁忌语,以便使它们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通过标注、封装、抑制这些想法,基底神经节解决了这样一个悖论,即为了了解什么是不该加以思考的,人们却不得不去思考那些不该思考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无法按照指令做到“不要去想一头大象”。正常情况下,基底神经节能够利用一个“不要去那里”的指令将我们的坏思想和坏行为巧妙地隐藏起来。但是,当基底神经节遭到削弱时,它们的加密锁和安全制动装置就会瓦解,于是,那些被我们标注为不可思议的或不能说的想法就会肆意地溜达出来。
在未受损伤的大脑中,大脑操作系统(包括前额皮质和大脑边缘系统的另一个部分,即前扣带皮质)能够对大脑的其他部位发出的行动实施监视,并将其拦截在途中。当彬彬有礼的朋友们一起聊天时,或者当一个牧师和老处女碰了自己的脚趾头时,那些从他们嘴里溜出来的、略有删减的咒骂(truncated profanities)就是这么来的:每一句标准的污言秽语都会提供一些删减后的替换选择。
god的替换选择:egad、gad、gadzooks、golly、good grief、goodness gracious、gosh、Great Caesar's ghost、Great Scott
Jesus的替换选择:gee、gee whiz、gee willikers、geez、jeepers creepers、Jiminy Cricket、Judas Priest、Jumpin’Jehoshaphat(传说中犹大国王的名字,表示惊讶)
Chris的替换选择:crikes、crikey、criminy、cripes、crumb
damn的替换选择:dang、darn、dash、dear、drat、tarnation
goddam的替换选择:consarn、dadburn、dadgum、doggone、goldarn
shit的替换选择:shame、sheesh、shivers、shoot、shucks、squat、sugar
fuck和fucking的替换选择:fiddlesticks、fiddledeedee、foo、fudge、fug、fuzz;effing、flaming、flipping、freaking、frigging
bugger的替换选择:bother、boy、brother
bloody的替换选择:blanking、blasted、blazing、bleeding、bleeping、blessed、blighter、blinding、blinking、blooming、blow
《卖花女》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管家皮尔斯夫人告诫亨利·希金斯不要在伊莉莎的面前说脏话。
皮尔斯夫人:……有一个特殊的词我必须要求你不要使用。因为洗澡水太热,那个女孩自己(伊莉莎)刚刚说出了它。它的首字母与bath的首字母相同。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这个词:她是在她母亲的膝盖上学会的,但她绝不能从你的嘴里听到这个词。
希金斯(傲慢地):我不能因为说过这个词就责备自己,皮尔斯夫人。(她死死地盯着他。他一边用一种公正的样子掩饰着内心的不安,一边补充说)也许除了在极端兴奋的时刻。
皮尔斯夫人:就在今天早上,先生,你就将这个词用在你的靴子、黄油和黑面包上了。
希金斯:哦,原来是那个啊!那只不过是为了押头韵而已,皮尔斯夫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诗人们所说的那些自然的修辞手段实际上是大多数禁忌词语的委婉形式的来源。在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改了调的脏话列表中,是头韵(alliteration)和谐音(assonance)在起着积极作用。就是这个韵律将bloody变成了ruddy、son of a bitch变成了son of a gun。此外,我们还有其他几十个伦敦俚语中禁忌语的委婉说法也是这样演变出来的,比如,raspberry(树莓,源自raspberry tart,树莓馅饼)替代了fart、Friar(男修道士,源自Friar Tuck,塔克修道士)替代了fuck。还有法语中那个老套的脏话Sacre bleu!变成了委婉说法Sacre Dieu。
一般来说,这些诗学手段通常会对我们心智中某种组织词语的心智结构进行重复,比如,音节首辅音(onsets)、韵律(rimes)、音节尾辅音(codas)。音位学家已经甄别出另一些更复杂的结构,构成一个单词的音节被连接到一个界定这一单词的节拍及其结构的骨架上。在诗歌或修辞中,当一个语言框架的部分被重复时,这就是所谓的平行结构,就像第23首《圣经》诗篇中所描写的He makethme to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He leadeth me beside the still waters(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来到安静的溪水边)那样。在咒骂的王国里,这种平行结构在无数胡说八道的委婉表达式中随处可见,这些委婉形式所共享的只是这种结构的韵律和形态结构。许多表示“伪善”的术语都是由两个重读单词构成的合成词,它们要么是单音节词,要么是首音节重读的一重一轻的单词。
applesauce(胡说)、balderdash(胡言乱语)、blatherskite(爱说废话的人)、claptrap(讨好的)、codswallop(废话)、flap-doodle(瞎说)、hogwash(废话)、horsefeathers(胡说八道)、humbug(骗子)、moonshine(突谈)、poppycock(废话)、tommyrot(无聊)
谩骂术语的另一个来源是语音象征。人们在谩骂时,往往会使用那些听上去既快又刺耳的语音。它们往往是单音节或首音节重读的单词,并且往往包含短元音和阻塞音(stopconsonants),尤其是/k/和/g/这两个爆破音。
fuck、cock、prick、dick、dyke、suck、schmuck、dork、punk、spick、mick、chink、kike、gook、wog、frog、fag
pecker、honky、cracker、nigger、bugger、faggot、dago、paki
20世纪70年代,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见过这样一张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NO NUKES(禁止核武器),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术语,于是他竟认为那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口号!休斯指出:“尽管下面这一观点可能会遭到合理的反对,即多数谩骂行为并非独创……不过,它与诗意之间的某些亲密关系确实可以被观察到。在谩骂与诗歌创作这两个领域中,语言的使用不仅是高负荷的,而且都极具隐喻性;它们所表现出的极致和锐利的效果都是通过压头韵,或者通过挑起词语在不同语域间的对抗而创造出来的,而且韵律至关重要。”
咒骂语义学
既然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一些有关咒骂语言学、咒骂心理学、咒骂神经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就能找到一条有关诅咒的含义与用法的共同主线了呢?是的。一条最明显的主线就是它们带给人们的强烈负面情绪。由于人们对语言的感知是在无意识或者下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他们的注意力会不知不觉地被某个禁忌词语所捕获,并被迫去思考其令人不爽的内涵。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只要与他人交流,我们就有可能遭受精神上的打击,就好像我们被绑在一张椅子上,随时都有可能遭人一击。要想彻底搞清楚咒骂这种语言现象,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什么类型的想法会令人感到沮丧;第二,人们为什么会希望将这些不愉快的想法强加于人。
说来也怪,宗教竟然是英语及其他许多语言的咒骂语的发祥地。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能得到印证,举例来说,《圣经》的第三诫就是个最好的证明。此外,hell(地狱)、damn(该死的)、God(上帝)、Jesus Christ(耶稣基督)等词语的风靡以及用于指称禁忌的许多术语本身:profanity(不敬的言语,非神圣的)、blasphemy(亵渎神明,字面意思是“邪恶的言论”,但在实际使用中指对神性的不敬),还有swearing(咒骂)、cursing(诅咒)、oaths(发誓赌愿),这些词原本是指借用某个神或其某个象征(另类地出现在天主教的诅咒中的词语,比如,圣体龛[tabernacle]、圣餐杯[chalice]、圣饼[wafer]等)的符咒来担保的意思。
在当今英语国家中,宗教诅咒行为几乎不会让人感到有任何惊奇之处。一句Frankly, my dear, I don't give a damn.(坦白地说,亲爱的,我根本不在乎)会惊得观众一片哗然的年代已经随风而逝了。今天,如果再有哪个角色被这样的语言所激怒的话,这只能说明他是个老古董了。宗教禁忌词语在民间的泛滥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最直接后果。正如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所评论的那样:“亵渎神明的现象不可能比宗教本身出现得更早;如果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的话,那么就让他去亵渎奥丁神试试吧。”因此,要想理解这些宗教粗口,我们必须站在语言祖先的角度上设身处地地想想上帝和地狱到底对谁来说才是真实的。[14]
Swearing(发誓/咒骂)和oaths(宣誓/诅骂)的字面意思是“某人对履行自己的承诺而作出的担保”。这个字面意思往往会将人们带入那个充满矛盾策略(paradoxical tactics)的奇爱博士的世界[15],在那里,人们出于个人利益,心甘情愿地自我设限(self-handicapping)。以承诺为例:如果你需要向别人借钱,你必须承诺归还;如果你需要某人为你生儿育女,并发誓放弃一切、一心忠于你,你就必须保证要以同样的忠诚对待对方;你也许需要与他人做生意,为了得到你眼下所需要的东西,作为交换条件,你就得承诺将来会如期交货或保证服务。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受约人(promisee)为什么要相信你呢?很显然,如果食言,受益者很可能是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假如你确实食言了,你就得自愿承担一种惩罚,而且这种惩罚的严重后果足以让你心甘情愿地信守自己的诺言。以这种方式,你的合作伙伴就无须通过你的口头承诺来判断你是否可信,他完全可以通过衡量你的利益得失来决定是否可以与你合作。
在当今社会中,人们用法律契约作为承诺的担保,如果违约,我们就得接受合同所规定的惩罚条款。贷款购房时,我们以房屋作为抵押,如果不能偿还贷款,银行就有权收回我们的房产。我们遵守婚姻法,如果遗弃或虐待配偶,他们就有权索要离婚赡养费并分割财产。我们缴纳履约保证金,如果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保证金就会被没收。不过,在我们有资格借助商业和法律手段执行合同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进行自我设限。担保承诺时,孩子们会使用那些最原始的说法,“如果骗你我就去死”。就成人而言,过去,他们常常用上帝的惩罚作为起誓,比如,May God strike me dead if I'm lying(要是我说谎,愿上帝赐我死)以及这句话的一些其他表达形式,例如,As God is my witness(上帝作证)、Blow me down!(太惊人了!)、Shiver me timbers!(你吓唬我!)、God blind me!(老天爷!)——英国人的blimey(天哪,blind me的缩略形式)就是由这个表达式衍生出来的。
人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曾一度坚信,上帝随时都在倾听他们的恳求,并会救赎他们,当然,在过去那些日子里,这些誓言会更可信些。可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即使他们信誓旦旦地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赌愿后食言了,上帝也不曾对自己实施过任何惩罚,于是,他们便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上真有上帝吗?上帝真的会救赎他们吗?退一步说,至少人们对上帝对他们的关注程度开始心存疑虑。当然,上帝在尘世的那些代言人们倒是宁愿人们保持之前的信仰,坚信上帝始终都在聆听自己的呼声,并会在大是大非面前救赎自己;他们希望人们相信,上帝的冷漠是因为人们不分事情的大小轻重,事事都要祈求保佑,而这让上帝觉得自己的威严受到了小视,因而心生不悦。而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的起誓也变得徒劳无功了。
既然没有上帝的直接托管代理,人们便可以更加圆滑地借用圣名来担保自己的承诺,他们拐弯抹角地将上帝扯进自己的讨论中。(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最奏效的威胁往往是那些隐性威胁。)人们将自己的信誉与上帝可能始终感兴趣的附属物联系在一起,比如,他的名字、他的象征、他的著述、他的身体部位,等等。于是便出现了以……的名义起誓(swearing by)和凭……发誓(swearing on)等诸如此类的起誓现象。即使在当今,美国的审判程序上仍然有这么一个步骤,证人将手放在《圣经》上起誓,仿佛在告诉人们,如果做了伪证,即使他可以侥幸逃脱法律的监督,却无法逃脱无所不知的上帝的眼睛,上帝一定会严惩他的。早些年间,英国人以耶稣殉难的名义起誓:他的血('sblood)、他的指甲、他的伤口(zounds)、悬挂他的吊钩(gadzooks)以及他的身体(odsbodikins)。此外,人们还会以十字架的名义起誓,这就是孩子们说的那句Cross my heart.(我发誓)的出处。不过,最有创意的还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写给苏格兰长老会的那句话:“我恳请你们,看在基督内脏的份上,相信你们自己也有犯错误的可能。”
即使人们并不相信这些誓言真的能够带来惩罚,但它们却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即蝇头小利的日常保证与重大事件的庄严承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保持一种宗教圣物的神圣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取决于一个社团中的每个成员对其宗教圣物的敬畏和虔诚。这需要一种对集体精神的控制,任何人都不能随随便便地看、想或者谈论一件神圣的东西。起誓时,人们将这一圣物牵扯到辩论中就是为了迫使对方去思考那些平时不会轻易去思考的问题,因此,这就意味着,说话人是绝对认真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人们过于随便地利用一种圣物发誓赌愿的话,那么它的神性就会受到这种语义膨胀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基于神圣统治的政权会采取各种手段遏制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反对“滥发誓”的法律可能会更受欢迎,因为人人都希望,在他们需要用誓言约束自己时,这种语言的威力能够发挥作用,而且,他们并不希望由于自己的滥用而使得这种语言的魔咒遭到解除。
现在看来,尽管以上帝的血和内脏之名发誓显得有些过于陈腐,但隐藏在其背后的禁忌心理却依旧鲜活。作为家长,即使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们也不会轻易地作出“我以我孩子的生命起誓”这样的承诺。只要一想到要以孩子的生命为代价,无论为了什么利益,人们都会觉得极其不爽,假如那个孩子恰巧是自己的,那么,这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人们大脑中的每一根神经都会站出来抵制这种念头。即使这只是个闪念,也会令他们毛骨悚然,不过,这种强烈的自我威胁感确实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可信度。普通禁忌心理学正是建立在人类难以接受背叛亲人或同伴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人们在以某种神圣为名进行起誓的过程中,无论它是一种宗教的象征符号还是一个孩子的性命,这种心态始终贯穿其中。由于语言加工是机械地进行的,用于神圣起誓的敬神话语——也就是swearing这个词的“发誓”的意思既可以被用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并震慑他人,也可以用来造成对方精神上的痛苦——这就是swearing的“咒骂”的意思。
另一个歧义动词cursing(诅咒)也是个宗教禁忌语。就像人们可以通过一句诅咒将任何形式的不幸或侮辱强加给他人那样,基督教将一种令人极其不爽的想法打包进各种诅咒中,并强加给他们的仇视者:这种想法就是他们可能会在地狱中度过来世今生。今天,Go to hell!(见鬼去吧!)和Damn you!(你这该死的!)已经演变成常见的温和修饰语,不过在很久以前,人们确实担心会被永远地处以烈火焚身、唇焦口燥的刑法,并终生与可怕的食尸鬼以及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和呻吟声为伴,在那些年代里,这些说法的冲击力远比现在大得多。从下面这些咒骂中,我们仍然可以依稀感受到那些诅咒人下地狱的话给当时的人们所带去的那股原始的冲击力,设想有人盯着你的眼睛说“我希望你因税务欺诈而被判处20年监禁。我希望你的单人牢房炎热潮湿、蟑螂泛滥,到处散发着粪尿的臭味。我希望3个恶棍和你同住在一间牢房,他们每晚都暴打并鸡奸你”如此这般。对于那些曾经相信地狱存在的人们来说,诅咒到底有多残酷?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时,我们真该感谢当今那些极端又头脑发热的人们手下留情,他们毕竟只是将自己局限于一小部分污浊物和性的陈词滥调之内,我之所以说它们是陈词滥调,是因为这些咒语的意象很久以前就已经枯槁了。
同样失去锋芒的禁忌语义场还包括疾病和瘟疫,例如,A plague on both your houses!(愿瘟疫降临到你们两家!/意为:你们两个都别说了!)[16]、A pox on you!(愿你脸上出水痘!/你该死!)以及波兰-意第绪语中的Cholerya!(愿你得霍乱!/不得好死!)。随着环境卫生大幅度改善以及抗生素的诞生,这些隐喻的杀伤力也变得越来越弱,人们很难再感受到它们曾经带给人们的那种致命的打击。不过,这两个语义场倒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中的那一场Bring out your dead!(拉[死于黑死病的]尸体的马车过来了!)的情节,或医学教科书中的脓疱、大出血、眼溃疡、腹泻以及与这些疾病有关的其他一些可怕症状。在现代社会中,与这类话语平行的说法大概包括这样一些诅咒:“但愿你陷入火海,让大火把你烧成三度重伤。但愿你中风抽搐,流着口水终生瘫痪在轮椅上。我希望你患上骨癌,在你的亲人面前油尽灯枯、气息奄奄。”看来,那些将发誓赌愿说成是文化粗俗化走势的标志的评论家们,应该再次反省一下他们的定论了,与上述提到的那些历史标准相比,我们今天的诅咒该是多么的温和淡雅啊。就这一点来说,我这里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很显然,现代人忌讳用癌症(cancer)这种最令人恐慌的疾病起誓。这个词已经衍生出了一些委婉语,例如,the big C(大C)、malignancy(恶性肿瘤)、neoplasm(囊肿)、mitotic figure(分裂象)等,此外还有一种常常出现在讣告中的说法:a long illness(长期患病)。
尽管人们已经不再以疾病的名义发誓,但体液、身体上的孔洞以及排泄行为等依然是人们借用于起誓的对象。Shit、piss、asshole等词语还是不能在网络电视中随便使用,或在报刊上出版发行。以《纽约时报》为例,这家报纸最近将哲学家哈利·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写的那本畅销书《论扯淡》(On Bullshit)改成了“On Bull——”。Fart也不比上面那几个词更被大家接受,《泰晤士报》已决定将其用于印刷体写成的old fart这个表示年龄歧视的表达式的一部分,而不是那个表示肠胃气胀的方言词。Ass、bum、snot以及turd也无一例外地游走于体面的边缘。
Bloody是另一让人联想起体液的词。正如许多禁忌语那样,没有人真正了解它到底出自何处,因为人们往往不会公开发表他们的不敬言辞。尽管如此,各种通俗语源学(folk etymologies)的无稽之谈从未销声匿迹过。就像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Fornication Under Consent of the King(国王应允的私通)以及Ship High in Transit(航海过程中升高货舱甲板)那样。以bloody为例,休斯曾说过:“我相信我并不是第一个(多次而且是十分有把握地)被告知bloody这个词起源于那句宗教惊叹By our lady!(圣母作证!)的词语爱好者。”然而,根据历史学家的观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它也同样不可能出自于God's blood(上帝的血)。
还有cunt,一些人始终搞不懂这个词怎么就变成禁忌语了呢。这个词不仅是对vagina(阴道的学术说法)的一种猥亵表达法,而且,对于美国妇女来说,它还是一个最具侵犯性的绰号;对于英联邦的男人来说,它也是个不大礼貌的术语。
一般来说,禁忌语的可接受性与它们所指称的物种的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是很松散的,不过,有关体内废物这一类的禁忌语却是个例外,它们能否被接受完全取决于它们的所指物。Shit(屎)比piss(尿)难于接受,piss(尿)比fart(屁)难于接受,fart(屁)比snot(鼻涕)难于接受,snot(鼻涕)则比spit(唾液,spit根本不是禁忌语)难于接受。这个顺序与人们对在公共场所的排泄物的可接受性完全一致。
针对人们对这些物质的反感程度,语言学家基思·艾伦(Keith Allan)和凯特·布里奇(Kate Burridge)对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大学的员工和学生们进行了问卷调查,希望以此扩大这项研究的调查范围。他们的调查结果如下:排泄物和呕吐物并列第一,女性经血排在第二位(男性的看法),尿液和精液名列第三。接下来的排列顺序为(按照递减顺序排列),胃肠胀气方面:脓液、鼻屎、经血(女性的看法)并列第四,紧随其后的物质依次为:打嗝的气味、皮屑、汗液、剪下的指甲、口气、伤口渗出的血液、剪掉的头发、母乳以及泪水。不过,它们与粗俗语的对应关系并不完美:尽管呕吐物和脓液均属于令人作呕之物,但英语中却没有关于它们的禁忌语。相反,与体内废物有关的粗俗词语却位居首位,其中包括有关精液的各种粗俗的说法,比如,cum、spunk、gizzum、jizz、cream等。
表示体内废物的这类词语在许多文化中都是禁忌的,当然也包括这些废物本身。生物学家瓦莱丽·柯蒂斯(Valerie Curtis)和亚当·比兰(Adam Biran)从他们在欧洲、印度和非洲所做的调查问卷中总结出如下的结论:“诸多报道中,身体排泄物都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的触发因子。全部调查列表中均有粪便,而呕吐物、汗液、唾液、血液、脓性液体以及性交产生的体液的出现频率也很高。”体内废物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特殊的情感纠葛,这种情感纠葛使它们与伏都教、巫术以及其他种类的交感魔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都相信,如果对一个人的粪便、唾液、血液、指甲以及毛发等施咒,这个人就会受到伤害;而假如这些污物受到诅咒、埋葬、淹没或者其他明显的抛弃,那么,人们就可以免遭伤害。由于这些物质在人们心目中的威力,他们还将与这些物质有关的词语应用到医药或符咒中,尤其是顺势疗法或净化的药剂中。厌恶情感与交感魔法心理是互相交织的。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和艾普利·法伦(April Fallon)的研究表明,在面对自己的厌恶反应时,比如,只要看到一种看起来令人恶心的东西或过去曾经碰到过类似的东西就不会去碰它,现代西方人往往会诉诸伏都教。词语魔法仅仅通过一种链接就能扩展这一联系链,并且赋予那些表示体内废物的词语一种可怕的魔力。
当然,人们的这种恐惧心理也是可以调节的,因为它毕竟只与性、医药、哺乳以及动物和婴儿护理有关。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委婉语的使用将逐渐淡化人们对这些物质的反感,脱敏运动有时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人类对自己体内废物(既包括它们的禁忌词,也包括这些物质本身)的异常反应令许多观察者们都感到不解。就像宗教学者莱因哈特(A.K.Reinhart)所说的那样:“出于某些原因,许多文化都倾向于将脓汁、呕吐物、小便、月经、性液体等体内废物看成是令人讨厌的物质或行为,尽管它们伴随着人类生活的始终,但人们却将其看成是变态的物质和行为。”柯蒂斯和比兰找出了其中一些原因。他们注意到,那些最令人恶心的物质往往是最危险的疾病传播源,他们认为这绝非巧合。粪便是传播病毒、细菌和原生动物的一种途径,原生动物至少能导致20种肠道疾病以及蛔虫病、甲型和戊型肝炎、脊髓灰质炎、阿米巴痢疾、钩虫病、蠕虫病毒、鞭虫、霍乱、破伤风等。血液、呕吐物、黏液、脓性液体以及性交体液对病原体同样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们往往被病原体当作人际传播的载体。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冲洗厕所和垃圾清运迅速地将我们与我们所产生的废物分离开来,但在其他落后国家,这些废物每年都会传播出无数的疾病。在战争时期或天灾横行的年代,比如2005年新奥尔良那场紧随卡特里娜飓风而至的大洪水,即便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人们也同样难免霍乱和伤寒病的威胁。
厌恶反应的最强烈表现就是不想吃或碰那些令人厌恶的东西。不过,只是想到那些体内废物、产生废物的身体器官与身体活动,人们同样也会感到恶心,而且,由于语言感知是无意识的,所以,一听到描写它们的词语,人们就会感到不爽。处于令人生厌之首的物质当属那些黏性物质,其次是尿液,而且piss(小便)这个词本身也属于一个轻度的禁忌语。尿液通常没有传染性,当然,它也是一种携带人体代谢物和毒素的废物,因此,它肯定不是讨人喜欢的东西。寄生虫是传播疾病的主要载体,它们因此遭到广泛的憎恶。毫不奇怪,它们的名字在英语的诅咒中随处可见,例如,老鼠、虱子、蠕虫、蟑螂、昆虫、鼻涕虫等,尽管它们还没有达到禁忌的地步。有关为什么这类词会成为某个特定文化和年代的禁忌语,而另一些词却并未遭此厄运的问题始终是个谜。也许禁忌语的习得只能发生在童年时代,或者充满情感气息的语境中。或许它们本身有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只要人们视它们为禁忌语,它们就永远保持着自己的禁忌身份。
禁忌词语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有关性方面的事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认为,这类禁忌实在太荒谬了。他们指出,性是一种共同快乐的源泉,它本不应该是件耻辱和羞愧的事。性语言的过分拘谨只能是一种迷信行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做法或者一种恶意的产物,就像门肯(H.L.Mencken)给“清教主义”下的定义那样:“它是对某人、某地可能是幸福的这种想法的一种驱之不散的恐惧。”莱尼·布鲁斯在他著名的独白Did you come?(你来/高潮了吗?)的结束语中说:“在这个房间里,如果有人发现不及物动词to come(来)是淫秽的、邪恶的、粗俗的——如果这个词真的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且你觉得我说这话很讨厌,那么‘你’很可能不能来(高潮)。”
对那些最常见的性诅咒,布鲁斯同样感到不解。
什么是你跟谁都能说的最糟糕的事情?“Fuck you, Mister.”这实在很奇怪,因为假如我真的想伤害你,我应该说“Unfuck you, Mister”。因为Fuck你实际上是件“好事”啊!“喂,妈,是我。是的,我刚回来。噢,fuck you,妈!当然,我是说真的。爸在吗?噢,fuck you,爸!”
布鲁斯的部分疑虑来自于fuck you的奇怪句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实际上并不是“发生性关系”的意思。此外,他的不解还来自于现代人(尤其是青年男子)对性在整个人类体验中所扮演角色的肤浅认识上。
试想两个刚刚做完爱的成年人,他们两人都开心吗?事实并不一定如此。一方可能会将做爱看成是一种终身关系的开始,另一方则很可能只把它当作一夜风流。而且,一方还有可能将疾病传染给另一方。不仅如此,这份激情还可能会造成意外怀孕,而这个胎儿并不是此次激情计划之中的产物。假如这对男女再有亲缘关系,那情况就更糟糕了,因为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继承同一个隐性有害基因的两个副本,而且极易受到该基因缺陷的影响。当然,即使没有怀孕的问题,还会有其他问题,比如,他们之间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个妒火中烧的情敌、一个处于为别人抚养孩子的危险之中的绿帽丈夫,或者一个处于失去抚养自己孩子权利的危险之中的不忠妻子。此外,其中一方的父母很可能已经为他/她安排了婚姻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涉及大笔金钱或与另一个家族的重要联姻。当然,还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这一对恋人并不都是成年人,或并不都是出于自愿的。
进化心理学为我们揭示了人类性行为中固有的利益冲突,其中的一些冲突是置身于语言领域之外的。直截了当地谈论性,这种行为所传达的是一种不严肃的性态度,即性不过是一种类似于网球或集邮之类的平凡小事而已,在性关系发生的时候,这种态度会被对方感受到。而天长地久的愿望则可能受到更大范围的相关人群的关注。对于父母和其他年长的家族成员来说,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家族传宗接代的计划是否会受到妨碍;而就整个社团来说,它所关心的则是性自由可能带来的婚外生子、竞争,甚至暴力等问题。一夫一妻制度下,尽管夫妻间的理性交流可能过于陈腐,甚至有些不切实际,但对于一个家庭的长者们和整个社会来说,毫无疑问,这种理性化的性交流是最有利于他们的统治的。因此,在谈论有关性方面的问题时,个人与社团的守卫者们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伴随着社团的守卫者们在涉及自己的草率性行为时的道貌岸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
性冲突在男、女之间的表现最为突出,它远远超过了年轻人与老年人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在这方面的冲突。我们是哺乳动物,而生殖的不对称性是这类动物的先天特征:在整个繁殖过程中,雌性必须致力于很长一段时间的妊娠和哺乳,而雄性则只需几分钟的交配便可以万事大吉。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他就可能会有很多后代;而如果一个女性与很多男性发生过性关系,她则不会有更多的后代——即使她选择了一个愿意为她的后代投资的伴侣,或者一个能够把良好的遗传基因传给下一代的伴侣。难怪男人在所有文化中都更加渴望性,更热衷于一夜情,更有可能采取引诱、欺骗或威逼等手段来获得性。对于男人来说,在所有条件均等的情况下,无论从遗传还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随心所欲的性行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不对称性在人们对性的闲谈中也应该有所表现,事实正是如此。就平均而言,男人更喜欢说脏话,而许多性禁忌语所带给人的感觉都是对女性的侮辱——因此才有了那个禁止在“妇女和儿童面前”说脏话的传统禁令。
男女对性语言耐受性的差别可能会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在听到粗俗的言辞时,她们会把手腕举到前额上,并随即昏倒在沙发上。由于扫黄运动语言指南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第二次大潮意外地复活了脏话对妇女的侵犯。格鲁乔·马克思如果知道当今的大学和企业已经实施了他在《鸭羹》(Duck Soup)中治理弗里多尼亚(Freedonia,《鸭羹》中一个虚构的国家)的纲领“不许吸烟或者讲黄色笑话”,他一定会大吃一惊的。许多公开发表的性骚扰指南都将“讲性笑话”列入其定义当中,1993年,仅仅因为一位女职员偶然在编辑部听到他对一个拒绝与他下班后一起去打篮球的男同事说了句pussy-whipped(怕老婆),《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资深记者大卫·尼汉(David Nyhan)被迫向一个妇女组织道歉,并捐赠给该组织1250美元。以激进的反黄主义闻名于世的女权主义作家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提议,一切性交行为均属强奸,均是对女性公然的性压迫:
性骚扰即男性对一个权力不及自己的人所实施的性行为,而且这种定性在这种性行为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使那个性行为的承受者蒙受耻辱……在男权社会体系中,性就是他们的生殖器,生殖器就是他们的性主权,而这种性主权在性交中的使用就是他们所谓的男子气概。
尽管维多利亚时期对性侮辱的过分讲究遭到了现代人的嘲讽,但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一种放荡的社会氛围中,受到伤害更多的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从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革命早期这10年间,许多流行文化的作品都以同情的手法来描写那些好色之徒,以此庆祝清教主义的彻底瓦解(乔·奥尔顿[Joe Orton]、汤姆·莱勒[Tom Lehrer]、伍迪·艾伦、滚石乐队的杰作以及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罗文和马丁斯的大家笑》[Rowan and Martin's Laugh-In]节目都是典型的例子)。重读这些创作,那些对女性的肆意伤害会让人感到痛心疾首。作品中的妇女们往往被描写成放荡不羁的荡妇或供男人取乐、骚扰、虐待的天生尤物。中产阶级文化中对这种淫荡行为的短暂赞颂(一端是年轻人对长者、个人对社会的挑战,另一端是女性对男性的挑战),部分地揭示了操控性语言所带来的利益冲突。
尽管当今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观赏、谈论或者亲身体验性行为,但性交这一话题仍然无法摆脱禁忌的身份。绝大多数人仍然不会在公共场合发生性关系、在宴会结束后交换配偶、与同胞兄弟或自己的孩子发生性关系或者公开进行性交易活动,等等。即使在性解放运动之后,对性的彻底探索仍然任重道远,而且,这意味着,人们对某些有关性的想法仍然心有余悸。而在人们设置这种心理障碍的过程中,性语言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诅咒的5种方式
有了上述这些关于禁忌语的基本内容(它的语义知识)为基础,现在我们就可以转向对其使用方法的探究了(它的语用知识)。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说过,所有诅咒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那些没有人愿意去体验的情感纠葛——敬畏感(针对上帝及其外部标志)、恐惧(针对地狱和疾病)、厌恶(针对体内废物)、仇恨(针对背信弃义的人、异教徒及少数民族)或者堕落(针对性行为)。由于言语感知是机械的,因此,只要听到一个禁忌词,人们就会被迫去思考一些平时不会去思考的问题。这个现象有助于我们研究脏话是如何被使用的,说话者为什么希望将自己的意志以这种方式强加给听众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人们至少会以5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诅咒:叙述性的(Let's fuck)、习惯性的(It's fucked up)、滥用性的(Fuck you, motherfucker!)、强调性的(This is fucking amazing)、宣泄性的(Fuck!)。让我们一个个地进行考察吧。
关于脏话的许多不解之谜归根到底都是一个问题:一个禁忌词是如何使自己有别于其他指称同一事物的文雅术语的?到底是什么激起了人们如此强烈的反应?举例来说,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使用feces而不是shit, penis而不是prick, vagina而不是cunt, have sex而不是fuck。
它们的主要差别就在于,禁忌词是恶俗的——它使人想到它所指称之物令人最不愉快的特征,而不仅仅是指称这个事物。对于排泄物来说,人们不仅讨厌看到它、闻到它、碰到它,就连想到它都会感到恶心。然而我们是肉体化身的生物,排泄恰恰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在某些场合下我们不得不共同商议处理它的办法,别无选择。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将委婉语(euphemisms,以不引起不良情绪的方法指称一个实体)和恶俗语(dysphemisms,包括禁忌语,被用于我们希望反复重申这个实体的讨厌程度的夸张场合)区别对待。
无论在物化方面还是传播方面,禁忌概念的委婉语和恶俗语都表现得相当迅速。据艾伦和布里奇的统计,到目前为止,英语已经积累了超过800个有关性交的表达式、1000个男性生殖器表达式、1200个阴道表达式以及2000个有关放荡女人的表达式(这是不是会让你怀疑,人们为什么还要对爱斯基摩语中有关雪的词语量大惊小怪呢?)。在当代英语中,我们还发现了几十个表示排泄物的专业术语,这大概是因为它既令人厌恶,又不可避免吧。
禁忌:shit
温和的粗俗语:crap、turd
温和的委婉语:waste、fecal matter、filth、muck
正式的表达式:feces、excrement、excreta、defecation、ordure
儿童的表达式:poop、poo、poo-poo、doo-doo、doody、ka-ka、job、business、Number 2、BM
尿布上的:soil、dirt、load
医学上的:stool、bowel movement
动物的,大单位:pats、chips、pies
动物的,小单位:droppings
动物的,科学的:scat、coprolites、dung
动物的,农业的:manure、guano
人类的,农业的:night soil、humanure、biosolids
大多数这类礼貌术语仅限于某种特定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那些排泄物不得不被提及,而且它们所涉及的行为恰恰适合这种语境(作为肥料播撒、换尿布、出于医学或科学的目的进行分析,等等)。因此,委婉语自然而然地带给这个话题一种亲近感。
就禁忌术语所指称的对象而言,英语表现得有些过于专门化,它没有给人们提供用于闲谈的中性表达方式。闲谈中,如果你的朋友使用的是feces、flatulence或anus等专业术语,而不是它们的禁忌替代词,那么,你即使只是在极端兴奋或情绪波动的情况下说了几句脏话,他们也会感到尴尬的。奇怪的是,其他所有与人体部位相符的盎格鲁-撒克逊词根在我们的日常用词中都可以找到,但阴茎和阴道却例外,当人们需要指称它们时,就不得不使用penis和vagina这两个拉丁语。正如刘易斯(C.S.Lewis)所说:“只要明确地涉及‘性’的问题,你就只能从托儿所、贫民区以及解剖课上的语言中间作出一种选择。”
当然在交流中,我们有时会希望提醒对方某事令人不爽之处,此时,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俗语了。还有的时候,为了使我们的叙事活灵活现或者出于愤怒,我们也会使用禁忌语,借此来形容一个事物到底有多么肮脏不堪。
那个管道工一边在水槽下面工作一边要跟我聊天,我只好一直看着他的屁沟(crack in his ass)跟他聊。
他的座右铭是:如果它(斗牛)冲过来,就X(fuck)它;如果它不过来,就刺(stab)它。[17]
把你的狗屎(dog's shit)捡起,别让你的狗在我的玫瑰花上撒尿(pissing)!
假如我们用委婉语(例如,臀部、性交等)将上述句子中的那些禁忌语替换下来,那么它们就会让人觉得缺少了些东西,因为我们替换掉的不仅是禁忌语,还有说话人的感情力量。由于禁忌词语唤起的是听众和读者心中的性欲细节,因此,它们常常被用于色情描写,或被许多成年男子用于激情的唤起请求:“说点刺激的。”
毫无疑问,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为特殊的修辞效果而储备禁忌词语。To swear like a sailor(像水手一样说脏话)、to cuss like a stevedore(像装卸工一样骂人)以及locker-room language(水手在储藏室里说的下流话)等语言表达式表明,说脏话是许多男权和蓝领阶层社交圈选择的语言。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诅咒将迫使听众去思考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它实际上是一种温和进攻的表现。因此,它与男人们在战乱时期炫耀自己的威武雄风、不畏牺牲的其他外部标志(沉重的靴子、金属钉、暴露的肌肉,等等)是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故意打破一些忌讳,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随和的气氛,即一种大可不必谨言慎行的交际环境。近几十年来,诅咒行为已经蔓延到了妇女和中产阶级阶层。(在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正赶上“代沟”问题的全盛时期,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曾对她说:“南希,你的嘴就像个厕所。”)事实上,这一发展趋势是20世纪追求不拘一格、男女平等以及男子气概和酷风尚传播的一部分。
禁忌语不仅能在人们希望向他人传达痛苦时唤起对方的情感反应,而且,当人们希望无故造成他人的痛苦时,它也同样可以大显身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侮辱、诅咒以及其他语言虐待形式中使用亵渎语言。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你会特别想威胁、惩罚或挫败他人的名誉。也许正是这种口头侵略的艺术将人们的语言本能训练得比任何其他类型的言语行为都更加富有生机,在许多文化中,它已经被提升到一个极其高雅的艺术层面。16世纪时,英国将这种口头侵略艺术称为“攻击性对诗大赛”(flyting)。请看下面这段莎士比亚风格的谩骂。
亨利亲王:……【你】这满脸红光的懦夫,这睡破床垫、坐断马背的家伙,你这座庞大的肉山——
福斯塔夫:他妈的!你这饿鬼,你这张小鬼儿皮,你这干牛舌头,你这枯槁的公牛鞭,你这干瘪的腌鱼!啊!我简直气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你这裁缝的码尺,你这刀鞘,你这弓袋,你这倒插的锈剑——
再请看意第绪语中的诅咒。
她应该怀石头而不是孩子。
愿你掉光所有牙齿,只剩下一颗留着牙疼。
他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医生。
在打造一句诅咒时,那些能够引起听众或旁观者不爽的词语随手可及,它们方便得让人根本无法克制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禁忌词会大量出现在诅咒中的原因。人或人体部位可能被比作体内废物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器官和附件,比如:
piece of shit(讨厌的家伙)、asshole(很讨厌的人)、cunt(淫妇)、twat(娘们)、prick(蠢人)、schmuck(笨人)、putz(笨蛋)、old fart(老鬼)、shithead(脑残)、dickhead(白痴)、asswipe(笨蛋)、scumbag(人渣)、douchebag(变态)
人们可以被建议做丢脸的事情,如Kiss my ass、Eat shit、Fuck yourself、Shove it up your ass,还有那个我喜欢的Kiss the cunt of a cow(这个说法的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585年)。再如,I’ll rip your head off and shit down your windpipe(我要揪下你的脑袋塞进你的气管里),这句话是我在波士顿公共汽车站偶然听到的。对其他语言中的脏话调查结果揭示了与此类似的主题。接下来就是英语中那个最常见的淫秽诅咒语Fuck you了,不过,要想真正理解它的意思,我们必须仔细考察一下有关性的禁忌语。
英语中表示性的动词呈现出一种古怪的模式。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将fuck称作“一个用于描写人类行为中最及物动作的不及物动词”,它的古怪性就在于此。想一想有关性的及物动词——哪个符合John verbed Mary中的verbed这个及物动词的用法:
fuck、screw、hump、ball、dick、bonk、bang、shag、pork、shtup
它们听起来不是很好,是吧?说好听点儿,这些动词有些打趣或失礼的意味;说难听了,它们其实就是对人的侵犯。那么,在上流社会中,人们到底使用什么动词来指称做爱这一行为呢?
have sex、make love、sleep together、go to bed、have relations、have intercourse、be intimate、mate、copulate
上述动词均为不及物动词。英译中,指称性伴侣的词往往是由一个介词引入的:have sex with(与……发生性关系)、make love to(和……做爱)等。实际上,它们中的大多数动词本身连动词都不是,而是由一个有名无实的“轻动词”(light verb),例如,have(有)、be(是)或make(使得),加上一个名词或形容词构成的习语(在《疯狂英语》中,理查德·莱德勒问道:“To sleep with someone[与某人睡觉],是谁在睡觉呢?A one-night stand[一夜情],又是谁站着呢?”)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看到,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词语的选择是恪守礼仪的。但为什么社会礼仪一定要将某种东西授权得像一个语法结构那样令人费解呢?
这里,我们在第1章中对动词结构所做的分析又能派上用场了。还记得我曾说过,每一种句法构式都从一组微类(micro-classes)中选择适合它的动词,而每个动词都有一个与该构式本身的含义相符合的含义,二者至少隐喻性地兼容。那么,利用这一原理,我们是否可以从有关性的动词(即那些不同于传统语法的“系词性动词”[copulative verbs])的句法中发现一些人类性行为的蛛丝马迹呢?
礼貌习语都有一些泄露天机的语法特征。由于缺乏独特的动词词根,它们便无法指定一个动作特有的运动方式或效果类型。由于缺乏直接宾语,它们也无法指定受该动作影响的实体或被动发生改变的实体。不仅如此,它们的语义还是对称性的(symmetrical):如果约翰和玛丽做了爱,这就意味着玛丽也和约翰做了爱,反之亦然。因此,所有这些动词都可以出现在另一种不及物动词的替换构式中,在这个构式中,性爱伙伴并不需要通过介词引入,相反,它构成了一个复数主语的一部分:John and Mary had sex(约翰和玛丽发生了性关系)、John and Mary made love(约翰和玛丽做爱了)、John and Mary were intimate(约翰和玛丽亲热了),等等。而那些具有同样句法特征的、与性无关的动词的语义则属于一种联合自主行动(joint voluntary action),例如,dance(跳舞)、talk(说话)、trade(贸易)以及work(工作):John danced with Mary(约翰与玛丽跳舞)、John and Mary danced(约翰和玛丽一起跳舞),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心理模型中,礼貌性动词预设着性是一种未指定方式的、双方共同参与的活动。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那些与性有关的粗俗及物动词。回忆一下我们在第1章中的发现,及物动词所描写的是一个故意对一个实体实施侵犯、影响,或者既侵犯又影响的施事者。尽管fuck与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那5类及物动词都不完全符合,但它确实与运动-接触-效果(motion-contact-effect)那类动词微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可以被意动类(conative)、物主提升类(possessor-raising)或者中间构式(middle constructions)所接纳,但却不能进入接触格构式(contact-locative)和反使役构式(anticausative construction)中。这与fuck这个动词在古斯堪的那维亚语中表示beating(有节奏地伸缩)、striking(敲打)或者thrusting(插入)的动词词源学是一致的,此外这与fuck的两个及物同义词bang和bonk是动词这一事实也是符合的。
如果描写性的及物动词意味着其直接对象受到了影响,那么,准确地说,它到底是怎样受影响的呢?我们可以从莱考夫对性动词参与概念隐喻的方式所做的分析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许多性及物动词都可以被隐喻性地用来指称不择手段地利用(exploitation),这一隐喻还包括:I was screwed(我完蛋了)、They fucked me over(他们耍了我)、We got shafted(我们受骗了)、I was reamed(我被X了)以及Stop dicking me around(别逗我了)。
这些性及物动词的另一个隐喻性主题是严重的伤害,例如,fucked up(彻底完蛋了)、screwed up(搞砸了)、buggered up(搞糟了)以及英国人说的bollixed(搞乱了)和cockup(一团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中的俚语包括首字母缩略词snafu、tarfu(Things Are Really Fucked Up,简直他妈的一塌糊涂)、fubar(Fucked Up Beyond All Recognition,乱得他妈的面目全非)。后来,这些术语被工程师们采纳,并成为他们的行话,现在,当计算机程序员在创建一个临时文件或教初学者命名一个临时文件时,他们往往会使用foo.bar——有点儿书呆子气的幽默。性及物动词背后的隐喻就是“发生性关系就是不择手段地利用某人”、“发生性关系就是伤害某人”。
许多其他语言中也都有这些概念隐喻。在巴西葡萄牙语中,fuck的粗俗等价词是comer,“吃”的意思,这个单词也是以男性(或采取主动的同性恋伙伴)做主语。假如站在交配力学隐喻的角度,这个动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应该是女人身体隐喻性地吃男人的身体。不过,它却符合人们对性行为的理解,因为在性交过程中,总是女人被男人所享用和开发。
因此我们可以说,性动词的句法揭开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心理模式。第一种模式让人联想起性教育课程、婚姻手册及其他更为社会认可的观点:性是一种细节不明的共同活动,是两个平等伙伴的交互参与。第二种性心理模式则比较阴暗一些,它介于哺乳动物生物社会学与德沃金式女权主义之间:性爱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为,它在一个主动的男性的鼓动下发起,并对一个被动的女性实施影响,其中的女性要么被不择手段地利用,要么遭到严重的伤害。两种模型均捕获了人类性行为的全部临床表现,假如语言真是我们思想模式的向导,那么我们便可以说,第一种性心理模式是公共话语所许可的,而第二种模式是禁忌的,尽管它在私下里还是会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正如我所说的,纯粹恶俗语与跨域到禁忌中的术语之间的界线是很难判断的。对许多人来说,excrement的内涵远比shit令人作呕,因为excrement专供描述污秽和肮脏之物,而shit则可以被广泛地用于习语和非正式语境中。然而,尽管如此,shit还是比excrement更令人难以接受。同样,被冠以fuck的行为带给人的不安程度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被冠以rape的行为相提并论,可是rape连禁忌词都不是。人们将一个令人不爽的词处理成禁忌语的习惯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一旦有人将其处理成禁忌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因此,这些词语的身份也许只能听任那个决定着一般词语和名字命运的“兴衰”的流行病学的摆布了。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尽管禁忌词唤起的是人们头脑中关于它们的指称对象最糟糕的印象,但并不会因此而遭到人们的排挤。禁忌身份本身就赋予了它们一种情感上的活力,这与它们所实际指称的东西毫不相干。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数习语中都包含着禁忌术语。一些习语还将这些术语的某些令人不快的方面隐喻性地投射到话语的主题上,例如,bullshit(胡说)、They fucked me over(他们耍了我)、He pissed on my proposal(他亵渎我的提议)、She pissed away her inheritance(她把遗产挥霍殆尽)等。然而,更多的习语并不这样,出现在它们当中的那些禁忌词只起到了激发听众兴趣的作用。
He went through a lot of shit.(他经历了很多挫折。)Tough shit(糟透了!)We’re up shit's creek.(我们进退维谷。)We’re shit out of luck.(我们倒霉透顶了。)A shitload of money.(一大笔钱。)Shit oh dear!([新西兰英语]天啊!)Shit, eh?([新西兰]祝你好运。)Let's shoot the shit.(有空一起扯扯皮。)Let's smoke some shit.(让我们吸这狗屎的烟。)Put your shit over there.(我们倒霉透顶了。)A lot of fancy shit.(许多花哨的东西。)He doesn't know shit.(他什么都不懂。)He can't write for shit.(他什么也写不了。)Get your shit together.(收拾一下你的烂摊子。)Are you shitting me?(你耍我呢?)He thinks he's hot shit.(他以为他有什么了不起。)No shit!(胡扯!)All that shit.(全是狗屎。)A shit-eating grin.(吃屎的笑容。)Shitfaced[drunk].(烂醉如泥。)Apeshit.(发疯。)Diddly-shit.(废物。)Sure as shit.(肯定。)
It's piss-poor.(太差了。)Piss off!(滚!)I'm pissed at him.(我生他的气。)He's pissed off.(他被惹怒了。)He's pissed.(他喝醉了。)Full of piss and vinegar.(朝气蓬勃。)They took the piss out of him.([英国]他们嘲弄他。)
My ass!(才怪呢!)Get your ass in gear.(挪挪你的屁沟。)Ass-backwards.(搞错了。)Dumb-ass.(蠢驴。)Your ass is grass.(你死定了。)Kiss your ass goodbye.(滚蛋吧。)Get your ass over here.(快点过来。)That's one big-ass car!(一辆超大的车!)Ass-out[broke].(一毛不剩。)You bet your ass!(你太他妈的对了!)A pain in the ass.(眼中钉。)
Don't get your tits in a tangle.([新西兰]用不着这么激动。)My supervisor has been getting on my tits.([英国]我导师总是无缘无故地跟我发火。)
Fuckin-A!(操!)Aw, fuck it!(噢,他妈的!)Sweet fuck-all(操她妈的!)He's a dumb fuck.(他是个白痴。)Stop fucking around.(别瞎胡闹了。)He's such a fuckwit.([新西兰]他就这么白痴。)This place is a real clusterfuck.(这地方一塌糊涂。)Fuck a duck!(去你的!)That's a real mindfucker.(那可真是个痛苦的局面。)Fuck this shit.(真他妈的见鬼。)
在词典编纂者杰西·薛洛尔(Jesse Sheidlower)所编辑的专业词典《脏词》(The F-Word)中,类似于上述这种类型的词条至少有250个。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隐喻和习语可以凝炼成无须进一步分析的公式。这一点似乎已经在这些粗俗习语上(至少部分地)得到了验证,在禁忌语的冒犯使用方式中,连同fucking amazing(太他妈的让人震惊了)这样的咒骂语,它们构成了最温婉的表达方式。
禁忌词对情感的超强影响力使得它们进入了一个同义词的怪圈:即使在语法或语义方面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也可以在习语中彼此替代。我猜测,许多令人不解的不合语法的脏话一定源自一些更可理解的宗教脏话,尤其当它们在从宗教到性以及污秽的咒骂的转变过程中时。
Who(in)the hell are you?(你到底是谁?)→Who the fuck are you?(你他妈的是谁?)(Also:Where the fuck are you?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Get the fuckout of here, etc.)(亦作:你到底他妈的在哪儿?你到底他妈的在干啥?给我滚出去,等等。)
I don't give a damn.(我根本不在乎。)→ I don't give a fuck;I don't give a shit;I don't give a sod.(我才不在乎。)
Holy Mary!(天哪!)→Holy shit!Holy fuck!(天哪!)
For God's sake(看在上帝的份上)→For fuck's sake;For shit's sake(他妈的)
就禁忌词语间的内部关系而言,它们的内涵要比语义或句法更能说明问题。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英语脏话句法中的两个重大奥秘:fuck在Close the fucking door(关上那该死的门)和Fuck you!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对于这些难解之谜的探讨最初见于纪念文集:《关于胡言乱语的研究:值此詹姆士·D.麦考莱诞辰33或34年之际献给他的诽谤文章》。它可以称得上是学术史上最新奇的一本文集了。已故语言学家吉姆·麦考莱(Jim McCawley)是生成语义学的创始人之一(此外还包括当代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哈吉·罗斯[Haj Ross]等人)。麦考莱的贡献包括一本名为《语法理论三千万》(Thirty Milion Theories of Grammar)的指南、一本名为《语言学家们一直想了解(但都羞于咨询)的全部逻辑问题》(Everything That Linguists Ha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ogic[But Were Ashamed to Ask])的初级读物和一本《食者的汉字指南》(The Eater's Guide to Chinese Characters),最后这本是教授读者用中文菜单点菜的指南手册。1971年出版的这本纪念文集中汇集了众多的反常规文章,其中有几篇是麦考莱以笔名Quang Fuc Dong和Yuck Foo(这两个名字据说都是他所创作的虚构的南河内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的名字)所创作的。在这部文集中,尽管有些诙谐和实例令人一知半解和乏味,但麦考莱对英语禁忌表达式所做的精细的语法分析,至今仍被学术研究所引用(有时被称为“Quang[1971]”或“Dong, Q.F.”)。
感叹词,如bloody(非常的)和fucking(他妈的)也许是闲谈中最常用的禁忌词了,尽管它们的语义和语法都很荒唐。一本有百年历史的英国俚语词典对bloody这个词条做了如下的定义:“最常见的……因为在伦敦底层人口中,每两到三个音节中就会反复乏味地出现一次这个词;它的使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更不用说什么血腥的含义。”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对一种叫作Fuck Patois(他妈的方言)的方言也做过类似的观察,比如,在一个关于士兵的故事中,那个士兵说:“I come home to my fucking house after three fucking years in the fucking war, and what do I fucking-well find?My wife in bed, engaging in illicit sexual relations with a male!”(打了他妈的三年仗,我他妈的回到了家,进了该死的房间,我他妈的看见了什么?我的妻子正在床上和一个男的胡搞呢!)
这种扮演咒骂角色的fucking语法成了2003年的头版新闻,当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播了金球奖的实况,爱尔兰老牌摇滚乐队U2的主唱波诺发表了如下感言:“This is really, really, fucking brilliant”(这他妈的实在、实在太好了。)事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并没有马上处罚有关媒体,因为他们的相关指南将“下流”定义为“描述或描绘性或排泄器官或活动的语料”,而波诺对这个fucking的使用属于“强调一种感叹的形容词或虚词”。然而,文化保守派对此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加州参议员道格·奥赛(Doug Ose)还试图利用美国国会规定的最污秽的法案,即《清洁电视广播法案》来弥补委员会的这一漏洞:
法案
对《美国法典》标题18项中的第1464款进行修正,并为某些亵渎广播节目的行为提供惩治条例及其他用途。
国会会议中,众议院和参议院代表制定了如下法案:《美国法典》标题18项的第1464款现修正如下——
(1)通过在“任何人”前面插入“(a)”,并且(2)在此条款的结尾处补偿如下内容:(b)本条款规定,就语言而言,profane(亵渎的)这个术语的内容包括英语单词shit、piss、fuck、cunt、asshole以及短语cock sucker、mother fucker、ass hole以及这类词和短语相互使用,或者与其他词或短语或其他语法形式(包括动词、形容词、动名词、分词和不定式形式)相互使用。
不幸的是,对于奥赛议员来说,该项法案丝毫没能弥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那个漏洞,因为它未能恰当地指定波诺所说的那句脏话的句法(更不用说法案里面cocksucker、motherfucker以及asshole的拼写错误,或者将它们认定为“短语”的错误)。
《清洁电视广播法案》假定fucking是一个分词性形容词(participial adjective)。遗憾的是,这是个错误。正如Quang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真正的形容词来说,比如lazy(懒惰的),你可以将它们交替地用于这样两种构式中:Drown the lazy cat(淹死那只懒猫)和Drown the cat which is lazy(把那只懒惰的猫淹死)。但Drown the fucking cat(淹死那只该死的懒猫)肯定不能与Drown the cat which is fucking(淹死那只正在发情的懒猫)替换使用。同样的,Drown the bloody cat(淹死那只该死的懒猫)并不意味着Drown the cat which is bloody(淹死那只血腥的懒猫)。你也不能说The cat seemed fucking(那只猫似乎他妈的),或者How fucking was the cat?(那只猫有多么他妈的?),或者the very fucking cat(那只非常他妈的猫),这是3个经常用来测试形容词词性的小实验。
一些批评人士还对《清洁电视广播法案》中另一个语法上的无知进行了调侃。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短语fucking brilliant(太他妈的好了)中的fucking应该是个副词,因为它修饰的是形容词,英语中只有副词才能修饰形容词,就像下面短语中的副词那样:truly bad(确实很坏)、very nice(非常好)、really big(确实很大)。然而,在上面的profane一词的定义中,奥赛恰恰忘了将“副词”这一语法范畴包括进去了!碰巧,禁忌感叹语(expletives)也确实不是真正的副词。关于胡言乱语的研究中的另一篇文章指出,尽管你可以说That's too fucking bad(太他妈的糟糕了)和That's no bloody good(不咋地),但你却不能说That's too very bad(那太非常坏了)或者That's no really good(那不真的好)。同时,正如语言学家杰弗里·纳恩伯格(Geoffrey Nunberg)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你可以用very(太精彩了)来回答How brilliant was it?(到底有多精彩?)但你却永远也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How brilliant was it?”(到底有多精彩?)“Fucking”(他妈的)。
还有比这更反常的情况,禁忌感叹语竟然还可以出现在一个单词或一个合成词的中间,举例来说,in-fucking-credible(难以他妈的置信)、hot fucking dog(热他妈的狗)、Rip van fucking Winkel(瑞普·凡他妈的温克尔)、cappu-fucking-ccino(卡布-他妈的-奇诺)以及Christ al-fucking-mighty(全能-他妈的-上帝)——英语中唯一一种利用中缀来构词(infixation)的情况。此外,bloody也能做中缀,例如,abso-bloody-lutely(相当绝对)、fan-bloody-tastic(相当奇怪)。威尔士作家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在他的回忆录《青年狗艺术家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Dog)中写道:“你总是能辨别出从大桥那端传来的布谷鸟的叫声……cuck-BLOODY-oo, cuck-BLOODY-oo, cuck-BLOODY-oo。”
禁忌感叹语的语义与它的句法一样离奇。bloody和fucking一般表达不赞成的意思,不过,这个反对却未必是针对那个被修饰的名词的。
面试官:英国食品为什么这么糟糕?
约翰·克里斯:因为我们要经营我们了不起的帝国,你明白了吗?
(Because we had a bloody empire to run, you see?)
克里斯实际上并不是在讽刺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他是在表达对英国食品很糟糕这一事实的嘲讽。同样,如果我说They stole my fucking laptop(他们偷了我该死的笔记本电脑),毫无疑问,我肯定不是在诅咒我的笔记本,它说不定还是个手感极佳的钛强力笔记本呢(苹果),17寸的显示屏、1.67千兆赫的处理器。禁忌感叹语所传达的信息是,整个事态,而不是由那个名词所命名的实体令人不开心,尽管那个实体与整个事态有必然的联系。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说这个情况令人不爽,一定是站在说话者的立场上的,而绝不是这个句子所提及的任何其他人。如果有人告诉你John says his landlord is a fucking scoutmaster(约翰说他的房东简直就是个他妈的童子军团长),你应该将他对童子军团长的不敬归罪于向你报告的那个人,而不是约翰,尽管fucking被用在了传达约翰话语内容的从句里。
这一语言难题的部分解释是,bloody和fucking这样的禁忌感叹语很可能是在禁忌语更新换代的过程中产生的(尽管它们之间并没有相同之处),比如,允许Where in hell(究竟在哪)转变成Where the fuck(究竟在哪)、Holy Mary(圣母啊)转换成Holy shit(天啊)的过程。就fucking scoutmaster(他妈的童子军团长)或者bloody empire(了不起的帝国)中的禁忌感叹语而言,它们的历史源头很可能是damned(该死的)或God-damned(该死的),在一些表达式中,它们现在依然存在,例如,Damn Yankees(该死的美国佬)、They stole my goddam laptop(他们偷了我该死的笔记本电脑),还有abso-goddam-lutely(绝对地)。Damn是在damned的虚缀-ed被吞音并在感知上被忽视的情况下演变而成的,例如,ice cream(冰激凌)、mincemeat(甜馅)、box set(盒子布景),它们之前分别为iced cream、minced meat、boxed set。如果有什么东西是被诅咒的(damned),那么它就是该受谴责的、值得怜悯的、不再有世俗用处的。fucking、bloody、dirty、lousy、stupid这些与damned有着类似情感弦外音的词语能够让人联想起damned的含义。因此,在英语史上,一旦某些宗教禁忌感叹语失去了锋芒,它们便与damned一道将其取而代之。
这一语言难题的另一部分解释方案是,富载态度(attitude-laden)的词语有时会躲开标准的语法机制,即在句法树形图上通过词语的组织顺序来计算“谁对谁做了什么”的语法机制。克里斯托弗·波茨(Christopher Potts)等语言学家主张,英语语法不仅允许说话者在一句话中作出断言——什么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且还为他们提供对该断言发表个人评论的科学方法。这些方法有时被称为规约含义(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它允许说话者表达自己对正在谈论的事情的态度,比如,他对结果的意见或他对参与者之一的尊重程度。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允许一个富载态度的词语摆脱被描写事件中的人物,转而倾向于说话者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我说“苏相信那个混蛋戴夫得到了晋升”,这很可能意味着苏对戴夫有着很高的评价,但它同时暗示着,我并不这么看待戴夫。这恰恰就是fucking和bloody这样的禁忌感叹语的解释方案。
禁忌术语的可更新性(swappability)还可以用来解释Fuck you之谜。还记得伍迪·艾伦那个诅咒司机的笑话吧——“多子多孙,枝繁叶茂,见你的鬼去吧”,这个笑话假设Fuck you是第二人称祈使语气,就像Get fucked(去死吧)或者Fuck yourself(滚)那样。莱尼·布鲁斯也作过同样的假设,正如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在他那本令人赏心悦目的小书《母语:英语以及来龙去脉》(The Mother Tongue:English and How It Got That Way)中所写的那样:
英语的非凡表现就在于它既囊括了无稽之谈,也囊括了令人神清气爽的事物。我们的语言有一个不被人知的怪癖好,当我们希望表达自己的极度愤怒时,我们会恳请我们的愤怒目标去做一件解剖学上不可能的事情,更有甚者,我们甚至会恳请它去做一件势必让它快乐无比的事情。你想想,还有什么能比Get fucked更不可思议的情绪吗?我们有时也会咆哮着说“祝你发财”或“祝你好心情”。
Quang对上述理论进行了细化。首先,在第二人称祈使语句中,人称代词必须是yourself(你自己)而不是you(你)——麦当娜的那首流行歌曲题为Express Yourself(表现自我)而不是Express You(表达你)。其次,真正的祈使句,例如,Close the door(关上门),可以嵌入在许多其他构式中。
I said to close the door.
我说关门。
Don't close the door.
不要关门。
Go close the door.
去把门关上。
Close the door or I’ll take away your cookies.
关上门,否则我拿走你的饼干。
Close the door and turn off the light.
关上门,然后再关上灯。
Close the door when you leave tonight.
晚上离开的时候关门。
而Fuck you却不能这么用:
*I said to fuck you.
*Don't fuck you.
*Go fuck you.
*Fuck you or I’ll take away your cookies.
*Fuck you and turn off the light.
*Fuck you when you leave tonight.
此外,在第三人称宾语中,这种差别也可以被观察到,例如,Fuck imperialism!(X帝国主义!)。尽管可以通过一个共享宾语将两个祈使句联合在一起,例如,Clean and press these pants(清洗并熨烫这些裤子),但却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将一个诅咒语和一个真正的祈使句联系起来,例如,Describe and fuck imperialism(描述并X帝国主义)。
Quang并没有就Fuck you的民俗词源学观点——它是I fuck you的省略形式,进行任何评价(就像在引言中那个不耐烦的顾客和空姐的故事里所描写的那样)。很显然,这种民俗看法与“性是一种不择手段的利用或伤害”这一概念隐喻是相辅相成的,但遗憾的是,就语法来说,它却是讲不通的。首先,fuck的时态是错误的;其次,主语的缺失也是无法解释的;最后,语言中并不存在与此类平行的结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英语中,I fuck you曾经是一种常见的诅咒。
最简单的解释是,fuck you中的fuck与Where the fuck(究竟在哪)和fucking scoutmaster(他妈的童子军团长)中的fuck是一样的:对一个有着类似情感弦外音的老宗教脏话的更新。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一个最可能的词源就是Damn you(该死的),也许是God damn you(天罚你)和May God damn you(愿上帝惩罚你)的缩略形式。它原来的语义应该是一种第三人称的祈使含义May it be so(但愿如此),这个含义常见于祝福(May you be forever young[愿你永远年轻])和诅咒(May you live like a chandelier:hang by day and burn by night[愿你的生活像一盏吊灯:白天挂着晚上发热])。但其诅咒却渐渐融入到了对不满的整体声明中。正如Quang所说的,Fuck you不仅与Damn you类似,而且与仅仅表达说话者对某个对象的强硬态度的其他构式也相类似:To hell with you!(见鬼去吧!)、Shit on you!(去死吧!)、Bless you!(祝福你!)、Hooray for you!(为你喝彩!)以及那句常用的挖苦话Bully for you!(哦,你可真行!)
禁忌语的最后一个用途是宣泄——当人们感到莫名的痛苦、挫折或遗憾突如其来时,damn、hell、shit、fuck或者bugger等便脱口而出。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会说,这样可以“释放压力”或者可以帮助他们“宣泄愤懑”。这就是所谓的情感液压隐喻(hydraulic metaphor),这种隐喻还见于宣泄情感、寻找出路、大发雷霆时。尽管这种隐喻捕获了愤懑的感觉,但它却不能对这种情感本身作出解释。目前为止,神经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大脑中的血管或管道携带加热液体(除了复杂模式中的燃烧神经元网络以外)。而且,目前也没有哪个热力学定律能够解释为什么Oh和fuck能比Oh、my或者Fiddle-dee-dee(胡言乱语)的发音能更有效地消耗热量。
不过,在宣泄式辱骂的过程中,大脑的一些其他机制也会参与活动。举例来说,触角电生理反应(electrophysiological response)机制在人们刚意识到犯错时就开始启动了。这一机制源于前扣带皮质(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它主要参与对认知冲突的监测。在公开场合,认知神经学家称这种反应为“错误相关负电位”(Error-Related Negativity),而私下里,他们则称其为“狗屎波”(Oh-Shit Wave)。
一些构成哺乳动物愤怒基础的边缘环路也与此有关。其中一个边缘环路叫作愤怒环路,它始于杏仁核(amygdala)的一部分,下行通过下丘脑(那个极小的调节动机的大脑集群),然后进入中脑的灰质。这一愤怒环路最初封装着一种反射,这种反射能让一个突然受伤或遭围捕的动物对惊恐、伤害作出剧烈反抗,并且在逃离捕食者的过程中,它常常会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声。任何人不小心坐到一只猫身上或踩了狗尾巴都可能发现他们的宠物会发出一种新的声音,有时,它们还会在腿上留下爪痕或牙印。实验心理学对这种被称为挫折-攻击假设(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的观点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例如,当两只老鼠一同放进一只笼子里并对它们进行电击时,它们就会打架。当奖赏它们的食物被突然取出时,一只老鼠会对另一只老鼠进行攻击,这大概是出于对其他同伴突然窃取食物、空间或别的资源的适应吧。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潜在的大脑环路被保留了下来。在手术过程中,当病人大脑中的这一部位受到电刺激时,他们会表现出暴怒。
这里我们所谈的是一种关于宣泄式咒骂的假说。大脑愤怒环路起着对边缘系统与消极情绪相连成分的激活作用,因此,人类的疼痛或挫折感都来自于这里。与消极情绪相连成分包括具有强烈情感负荷的概念表征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词语,尤其是大脑右半球中那些积极参与负面情绪的表征和词语。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成分由一个基底神经节控制下的安全制动机制所控制,但这个制动机制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在强烈的神经冲动的作用下,它就会崩溃。因此,失去理智的人很难再做到谨言慎行。就人类而言,受控反应主要是禁忌语的脱口而出。我们前面说过,动物的愤怒反应中也包括一种可怕的尖叫。也许正是这些词语的火上浇油,再加上人们释放反社会情绪的冲动以及他们对吼叫的强烈渴望,才使得大脑中的那些负面概念最终以诅咒的形式(而不是那种传统的哺乳动物的尖叫)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当然,人们对剧痛的反应说明,人类这一物种仍然保留着动物的咆哮本能。)综上所述,宣泄式咒骂很可能源于那个被赋予了人类概念和发音惯例的哺乳动物的愤怒环路的串线(cross-wiring)。
这种串线假说有一个问题,即人们愤怒时发出的咒骂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约定俗成的。就像其他单词和公式那样,它们是基于记忆中声音和含义的一种组合方式,而这种组合方式是一个语言社团所共享的。当我们撞了自己的头,我们不会喊Cunt!或Whore!或Prick!,尽管这些话与shit、fuck、damn一样,都是禁忌词(实际上,在其他语言中,它们是人们脚被踩时所发出的喊叫的英文翻译)。同时,根据人们所遇到的不愉快事情的成因,这些脏话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当人们突然受到他人的侮辱时,他们会喊Asshole!(混蛋),而假如他们的手指被掉下来的热锅烫到或被捕鼠器夹住,他们就不会这么喊了。因此,宣泄式咒骂是有场合和语言专属的。就像皮尔斯夫人谈及伊莉莎使用b-word单词(bloody)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在母亲的大腿上,或更多情况下,是在父亲的大腿上学会这些用法的。在我4岁那年的某一天,我坐在爸爸身边的副驾驶座位上,车转弯时,车门被甩开了,我随即说了句:“哦,该死!”当时,我为自己能在这种情况下说出像大人一样的话而感到无比骄傲。可遗憾的是,话音刚落,我就遭到了父母的虚伪训斥,没办法,这也许就是做父母的特权吧。
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出于咒骂的目的而刻意去学一些特定的词语呢?换言之,他们为什么不让自己的愤怒随便去激活某个头脑中固有的古老禁忌语呢?事实上,语言中还有一种比宣泄诅咒更加普通的现象,即所谓的“脱口而出”(ejaculations)或称“应急叫喊”(response cries),我们这里所说的宣泄式咒骂只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请看下面这个词语列表。
Aha(啊哈)、ah(啊)、aw(哦)、bah(呸)、bleh(哦)、boy(嘿)、brrr(呵)、eek(呀)、eeuw(噢)、eh(嗯)、goody(太好啦)、ha(哈)、hey(喂)、hmm(嗯)、hmph(哦)、huh(哼)、mmm(嗯)、my(哎呀)、oh(哦)、ohgod(噢)、omigod(天哪)、ooh(哦)、oops(哎哟)、ouch(哎哟)、ow(哦)、oy(嗯)、phew(唷)、pooh(呸)、shh(嘘)、shoo(嘘)、ugh(啊)、uh(恩啊)、uh-oh(噢唔)、um(嗯)、whee(呦)、whoa(咳)、whoops(哎呀)、wow(哇)、yay(哇)、yes(是)、yikes(呀)、yipe(呀)、yuck(啐)
乍看起来,上述这些单词似乎并不怎么像真正的英语,它们倒像是一些人们在痛苦降临时所发出的本能叫声的意译形式(transliterations of the noises)。它们根本无法用于语法句,如*I like goody(我喜欢太好啦);*I hate ouch(我讨厌哎哟)。而且,其中许多单词还违反了英语的语音模式,例如,eeuw(噢)、hmph(哦)、shh(嘘)。它们甚至无法用于交换意见。
遗憾的是,它们确实是有着约定俗成的语音和语义的英语单词。人们热衷于对它们进行标准的改造,而不仅仅将其作为某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许多人甚至将漫画家们用于渲染人们惊厥的拟声形式也改造成这类感叹词,例如,Gulp!(狼吞虎咽)、Tisk, tisk!(看看看!)以及Phew!(唷!)等。感叹词的误用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外地身份,比如在谈话间,一个说着流利法语的美国人错误地使用英语中的um(嗯)或ouch(哎哟)等。有这么一个笑话,在一个高级乡村俱乐部里,一个试图冒充欧裔美国人的犹太妇女走进了一个冰冷的游泳池。她不顾一切地大声喊道:“Oy vey!”(不,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呢。
与语言中的其他词语一样,oy vey以及其他应急呼喊词都是约定俗成的。当你看到一个可爱的婴儿,你会说什么?当你觉得周身发冷或者在送到嘴边的苹果里发现了一条虫子,你又会说什么?把餐巾掉在地上呢?或者发现开着的窗子正在往屋里刮着风呢?当一勺热汤暖遍了你的全身,你又会作何感叹呢?毫无疑问,针对上述情景,任何一个正常的英语使用者都能从前面那个列表中准确地选出一个恰当的感叹词。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苦心经营着自己在真实或假想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作为生活这个大舞台上的一个剧院评论家,社会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为我们分析了人们在生活这场大戏中的表演,尤其是他们的言辞。他指出,人们这种表演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旁观者们放心,自己是理智的、称职的、通情达理的,不仅如此,他们对当前的时局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理性的看法。一般来说,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就不能在公开场合自言自语,然而,在理性受到突发事件的挑战时,他们有时也会破例。就这一点而言,我有个很好玩的例子。我们有时会将该带的东西落在办公室,可是发现时却已经走到半路了,于是就不得不原路返回,这时,我们往往会喃喃自语,似乎在告诉身边的人,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瞎溜达的精神病患者。
高夫曼认为,人们之所以发出应急叫喊是有原因的:暗示同类,我们有能力且我们对某种情形的看法与他人是相同的。一个撞到玻璃的人很可能被认为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但如果他说了whoops(哎哟),那么至少能让我们知道,他是不小心为之,而且他对此感到很遗憾。如果某人把比萨酱撒到衬衫上,或者踩到了狗的粪便,然后说声yuck(啐),那么这个人至少比那些对此无动于衷的人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宣泄式咒骂也是如此。面对人生目标或幸福突如其来的挑战,我们告知世界,这次挫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事实上,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我们的情感层面上,因为它不仅会唤起我们最坏的想法,而且令我们濒于自控的边缘。与其他应急叫喊一样,破口而出的禁忌语也是按照挫折的严重程度校准的,shoot(唉)表示微不足道的烦恼,而fuck则表示相当严重的打击。按照人们对词语和说话口吻的选择,一句破口而出的禁忌语可以起到求救、恐吓敌人的作用,或者警告一个粗心大意的家伙,他正在无意中造成伤害。高夫曼总结说:“应急叫喊并不代表情感的宣泄,它所代表的是人们对同类事件看法的心照不宣。”
将宣泄咒骂看作是一种副产品的愤怒环路理论与将其看作是一种适应性的应急叫喊的理论其实并不矛盾。绝大多数应急叫喊也都是以约定俗成的语音表现形式出现的,例如,brr(哇)表示冷得牙齿打颤、yuck表示从嘴里面吐出来。这种仪式化很可能是构成宣泄式咒骂的基础。起初,这类诨名可能是由愤怒环路所释放出的禁忌词演变而成的,这些禁忌词从妥瑞症患者的口中脱口而出,随后被俗化成针对某一种冒犯或不幸的标准化应急叫喊,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宣泄咒语了。目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已经被一些认知神经科学家们再次采用,他们主张,语言化的爆发(verbalized outbursts)是灵长类动物的叫声向人类语言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缺失环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咒骂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要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关于诅咒的利弊权衡
那么,针对这些粗话,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咒骂的科学研究能否有助于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呢?比如,广播节目主持人语言低俗的问题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的净化与风化问题等。就政府的方针政策而言,我个人的言论也许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也毫无新意可言。在我看来,一方面,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惩罚或承诺人们对某些话语的使用并不是政府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根据人们的品位标准和市场需求,私营媒体有权强制执行一种独特的媒体风格,并将听众不喜欢的言辞排除在外。换句话说,一个艺人说fucking brilliant(太他妈的精彩了),这与政府毫不相干;如果有人不愿意告诉自己的孩子什么是口交,那么就应该为他们开设不会让他们感到为难的电视频道。这里,我并无意评论政府的相关方针政策,我只是希望就下面这个与语言相关的问题再谈谈我的看法,这个问题就是:禁忌心理语言学是如何帮助我们对什么场合下应该禁止脏话、什么场合下应该宽容甚至欢迎,作出合适的判断。
语言常常被视为一种武器,既然是武器,那么在瞄准何处、何时开火等问题上,人们肯定会三思而行。所有禁忌行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均属于一种将讨厌的想法强加于他人的行为。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认为到底多长时间向他的听众提及一次粪便、尿液和滥交这样的脏话是合适的。即使只是为了引人注目而说出的一句最温和懒散的脏话也同样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对于听众来说,那句话会令他们心烦意乱,而说话者却说,他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吸引听众注意力的办法了。那些作家们就更是过火,要知道,英语中有50多万个单词可供他们慢条斯理地进行选择。如果哪个记者在撰写关于东德斯塔西警卫的暴行时,选不出比fucker(混蛋)更恰当的名称来指称那个警卫,那只能说明他需要一本更好的同义词词典了。
还要提醒大家反思的是,语言禁忌是否总是一件坏事。为什么我们会遭到冒犯、为什么我们应当被冒犯——什么时候一个局外人士会用nigger来指称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用cunt来指称一个女人或者将一个犹太人指称为fucking Jew(该死的犹太人)?这些术语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它们的冒犯性也不可能来自它们本身。当然,它也不是对说话者令人生厌的态度的反应。当前,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直截了当地说出“我讨厌非洲裔美国人、女人和犹太人”来表达自己的反感,问题是,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对攻击目标的侮辱,倒不如说是对自己的侮辱,而且他们很快就会被当成令人憎恶的疯子。我猜想,人类的攻击意识很可能源于人们对语音识别和词语内涵的理解。如果你是一个英语使用者,当你听人说nigger、cunt或者fucking时,你肯定会联想到整个英语文化对这些词的理解,其中包括它们所隐含的情感意义。听到别人说nigger时,事实上就是在迅速地验证这样一个想法,即非洲裔美国人的身上有一些令人鄙视的品质,而且整个文化一致将这一判读标准定位在一个单词中。其他禁忌诅咒词也是这个道理:仅仅听到这些词语就会让人感到不道德,所以,人们不仅会将它们看成是令人不爽的言辞,而且还觉得根本就不该去想它们——这就是禁忌的真正含义吧。请注意,我并不是说这些禁忌词应该被禁止,而是我们应该理解并能预期它们给听众带去的影响。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祖辈遗赠给我们的语言为什么会在处理某些话题时表现得如此谨小慎微和缩手缩脚呢?回想一下,按照20世纪60年代言论自由者们的观点,禁止性语言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相当有害。他们辩称,将性行为从脏话中解放出来将消除人们的羞耻心和愚昧无知,从而减少性病、未婚生育以及性带来的其他危害。不幸的是,圣·莱尼的这种观点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性语言变得空前普及,然而,未婚生育、性传播感染、强奸以及性竞争所带来的附带结果(女孩子们的神经性厌食症和男孩子们的吹牛文化)却愈演愈烈。虽然没有人可以确定其中真正的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变化与人们对性的恐惧和敬畏的降低以及性禁忌语的解禁有必然的联系。
以上事实解释了我们重新审视诅咒问题的原因。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过度使用禁忌词语,无论是精心策划还是随心所欲,都将削弱它们的情感表现力,这就等于剥夺了人们拥有的一种必要的语言应急工具。这让我想起了那些诅咒赞成者们的论断。
首先,遭人类诅咒的都是些无法改变的事实。作家的义务是为人们呈现一幅“有关人性的、恰如其分的生动意象”,这其中包括当艺术需要的时候,他们必须对人物的语言加以如实的描写。1948年,在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写实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让士兵说脏话,那就会违背对他们的描写。然而,出于咒骂在当时的敏感性等问题的考虑,他还是采取了妥协。小说中,他让士兵们一律使用伪诨名(pseudo-epithet)fug(即fuck)。(当多萝西·帕克遇见作者时,她说:“你就是那个不知道fuck怎么拼的男人。”)可悲的是,这种谨慎的态度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专利。今天,一些公共电视台仍然不敢播放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有关蓝调音乐发展史的纪录片和肯·伯恩斯(Ken Burns)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其原因就是,在这两部片子中,作者与他们所采访的音乐家和士兵们都操着满口的脏话。广播媒体对脏话的禁令将艺术家和历史学家们逼成了骗子,不仅如此,它还颠覆了成年人探索世界的使命感。
为了令人信服地渲染人类的激情,即使他们的主人公不是士兵,作家们有时也必须让他发誓赌愿。在一部根据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伪情半生》(Enemies:A Love Story)中,一个甜美的波兰农村姑娘将一名犹太男子隐藏在一个干草棚里,当时正是纳粹占领时期,战争结束后,她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娇妻。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他有了外遇,而且还当着那个女人的面失控地打了自己妻子一个耳光。强忍着愤怒的眼泪,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救过你的命。在干草棚里,我把最后一口食物给了你。我为你端屎端尿(shit)!”此时,除了shit这个词,再没有其他任何词语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她对他忘恩负义的极度憎恨了。
对于语言爱好者来说,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不是他们享受脏话乐趣的唯一来源。任何一个习语都是某个有创意的前辈的脑力劳动的结晶,其中许多世俗化的表达方式都值得我们敬佩。我们真的应该放慢奔波的脚步,细心品味这些语言大师们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是他们赋予了我们的士兵shit on a shingle(鹅卵石上的炉渣,指军队里对抹在吐司上的熏牛肉片的描述)、我们的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忠告Keep your pecker in your pocket(把你的命根子揣好)[18]。还是这些语言大师们,他们所构思的这些表达方式是任何其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pissing contest(毫无结果的辩论)、crock of shit(一团狗屎,荒唐可笑的谎言)、pussy-whipped(受女人支配的,怕老婆的)、horse's ass(脓包,无能之辈)以及He doesn't know shit from Shinola(他不分狗屎和鞋油,意为毫无判断力、一无所知)。就评价人的言辞而言,下面这几位大师独特的遣词方式堪称首屈一指: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见长于描写那些令他不能信服的人,其中包括肯尼迪的助手(He wouldn't know how to pour piss out of a boot if the instructions were printed on the heel[如果指南印在了他的脚后跟上,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把靴子里的尿倒出去])、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 He can't fart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就连嚼口香糖和放屁他都不能同时进行])以及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 I’d rather have him inside the tent pissing out than outside pissing in[我宁愿让他站在帐篷里面往外撒尿也不愿意让他站在外面往里撒])。
脏话在诗歌中也同样奏效,比如,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74年的那首《这就是诗》(This Be the Verse)中关于“人们是如何手把手传递痛苦”的主题。
They fuck you up, your mum and dad.
They may not mean to, but they do.
They fill you with the faults they had
And add some extra, just for you.
他们搞出了你,你的老妈和老爸。
这也许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但他们确实搞出了你。
他们将自己的缺陷全部传给了你。
还苦心孤诣地增加了不少额外的不足,只为你。
这类语言还可以用于科学论证,比如,朱迪·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对孩子的人格是父母塑造的观点所作的如下反驳:
可怜的老爸老妈:公开地被他们的那个诗人儿子指责,却从未得到过任何机会为自己辩护。他们现在该有一次机会了,请允许我冒昧地为他们说两句:
How sharper than a serpent's tooth
To hear your child make such a fuss.
It isn't fair—it's not the truth—
He's fucked up, yes, but not by us.
多么锋利的牙齿,比蛇蝎还毒。
听到自己的孩子如此小题大做。
这不公平—也不是真相—
他确实被搞糟了,确实,但并不是被我们搞糟的。
这类语言甚至还可以用于抗议政府制裁脏话的处罚规定,比如,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艾瑞克·爱都(Eric Idle)的那首著名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之歌》(The FCC Song)。
Fuck you very much, the FCC.
Fuck you very much for fining me.
Five thousand bucks a fuck.
So I'm really out of luck.
That's more than Heidi Fleiss was charging me.
算你他妈的狠,联邦通信委员会。
你罚了我的款,我算你他妈的狠。
五千块钱X一次。
我着实倒霉透了。
这比海蒂·弗蕾丝要的价还高。
在众多表现逻辑学家们对词语的“提及”与“使用”之间的差异的例子中,这是我所听过的最直观的一个。
当咒骂被人们明智而审慎地使用时,它可以起到搞笑、一针见血、独具匠心的作用。它比其他任何语言形式都更能激发我们的语言表现力:句法的组合能力,隐喻的唤起能力,对押韵、节拍、韵律的欣赏能力以及对态度(意料之中的以及意料之外的)的情感操控能力,等等。此外,它还可以调动我们大脑的全部时空范畴:左右、上下、远古、当代。众所周知,莎士比亚以擅长诅咒闻名于世,他笔下的卡利班[19]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教会我人类语言,而我所收获的绝非一种语言而已,现在,我知道怎么骂人了。”就因为这句话,卡利班被莎士比亚塑造成了全人类的代言人。
